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张绍琪录入、整理
小引
世间事有不可已而已者,计利计害之鄙夫也;有可已而不已者,暴虎冯(ping)河之勇夫也。暴虎冯河,固为圣人之所不与,而计利计害,亦非君子之所乐为。顾其事之何如尔,事当其正,虽九死其如饴事,或非正,即万钟所不屑。斯可已不可已之辨,而鄙勇二者之失,皆可置之不问矣。唯于不可已之事,而不计利害生死,坚其不可已之志以行之,迹虽似乎徒搏徒涉之心,终为先圣后圣之所亮。此不可已之大中至正,当不可已者也。
世道之不替,赖士大夫以维之。士大夫者,主持世道者也。正三纲,守四维,主持世道者之事。士大夫既不主持世道,反从而波靡之,导万国为正法邪教之苗裔,而灭我亘古以来之君亲师,其事至不可已也。举世学人,不敢一加纠正,邪教之力如此重哉!三光晦,五伦绝矣。将尽天下之人,胥沦于无父无君也!是尚可以已乎?此而可已,孰不可已!斯光先之所以不得已也。较子舆氏之辩,其心伤,其情迫,何利害之足计,搏涉之云徒哉!故题其书曰《不得已》。
不得已 卷上
请诛邪教状
江南徽州府歙县民杨光先,年六十八岁,告为职官谋叛本国,造传妖书惑众,邪教布党京省,邀结天下人心,逆形已成,厝(cuò)火可虑,请乞早除以消伏戎事。
窃惟一家有一家之父子,一国有一国之君臣。不父其父,而认他人之父以为父,是为贼子;不君其君,而认海外之君以为君,是为乱臣。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况污辱君亲,毁灭先圣,安可置之不讨?西洋人汤若望,本如德亚国谋反正法贼首耶稣遗孽(一)。明季不奉彼国朝贡,私渡来京。邪臣徐光启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荐于朝,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谋渐张:令历官李祖白造《天学传概》妖书(二)。谓东西万国皆是邪教之子孙;来中夏者为伏羲氏,《六经》、《四书》尽是邪教之法语微言。岂非明背本国,明从他国乎?如此妖书,罪在不赦。主谋者汤若望,求序者利再可,作序者许之渐(三),传用者南敦伯、安景明、潘进孝(四)、许谦(五)。又布邪党于济南、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熟、上海、杭州、金华、兰溪、福州、建宁、延平、汀州、南昌、建昌、赣州、广州、桂林、重庆、保宁(今四川阆中市保宁镇)、武昌、西安、太原、绛州(新绛县)、开封并京师,共三十堂。香山澳盈万人,踞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伺朝廷机密。若非内勾外连,谋为不轨,何故布党、立天主堂于京省要害之地,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且于《时宪历》面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白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毁灭我国圣教,惟有天教独尊。
目今僧道香会,奉旨严革,彼独敢抗朝廷,每堂每年六十余会,每会收徒二、三十人,各给金牌、绣袋,以为凭验。(可能是圣名牌)光先不敢信以为实,乃托血亲江广,假投彼教,果给金牌一面,绣袋一枚,妖书(不是圣经!)一本,会期(教会历)一张。证二十年来收徒百万,散在天下,意欲何为?种种逆谋,非一朝夕,若不速行翦除,实为养虎贻患。虽大清之兵强马壮,不足虑一小丑,苟至变作,然后剿平,生灵已遭涂炭。莫若除于未见,更免劳师费财。伏读《大清律》“谋叛”、“妖书”二条,正与若望、祖白等所犯相合。事关万古纲常,愤无一人请讨,布衣不惜齑粉,效忠历代君亲,谨将《天学传概》妖书一本,邪教《图说》三张(六),金牌一面,绣袋一枚,会期一张,顺治十八年汉字黄历一本,并光先《正国体呈稿》一本,《张与许之渐书》稿一本,具告礼部,叩密题参,依律正法,告礼部正堂施行。
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告,本日具疏题参。堂司官亲带光先至左阙门引奏,随令满丁十二名,将光先看守在祠祭司土地祠。八月初五日密旨下部,会吏部同审。初六日会审汤若望等。一七日放杨光先宁家。(鳌拜辅政,后翻案是康熙亲政)
(一)如德亚国:指古犹太国。
(二)李祖白:字然真,天主教徒,官至钦天监夏官正。康熙四年被杀。其《天学传概》今罕传,台湾学生书局所出《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二册收有影印本。
(三)字仪古,号青屿,顺治进士,官至御史。康熙三年因杨氏此奏削籍,八年案雪复官。然性刚寡谐,径归。著《槐荣堂诗钞》等。
(四)潘尽孝;汤若望仆人,天主教徒。顺治十八年,因汤氏过继其子为义孙(名汤士宏),潘遂成为汤名分上的“义子”。
(五)许谦:明末是宫中太监,或即已入教,据德·魏特《汤若望传》,教名保禄。清初为满人博第家奴,住宣武门外,以卖烟为生。教案中一同受审,康熙四年三月逢大赦获释。
(六)“张”原作▪️,据清抄本补。
与许青屿侍御书
新安布衣杨光先稽首顿首,上书侍御青翁许老先生大人台下。士君子搦(nuò)七寸管,自附于作者之林,即有立言之责,非可苟然而已也。毋论大文小文,一必祖尧舜,法周孔,合于圣人之道,始足树帜文坛,价高琬琰(yǎn),方称立言之职。苟不察其人之邪正,理之有无,言之真妄,而概以至德要道许之,在受者足为护身之符,而与者卒有比匪之祸。不特为立言之累,且并德与功而俱败矣。斯立言者之不可以不慎也。吾家老不晓事,岂不可以为鉴哉?
兹天主教门人李祖白者,著《天学传概》一卷,其言曰:“天主上帝,开辟乾坤,而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孙聚居如德亚国,此外东西南北,并无人居。(依此说则东西万国,尽是无人之空地。)当是时,事一主,奉一教,纷歧邪说无自而生。其后生齿日繁,散走遐逖,而大东大西,有人之始,其时略同。(祖白此说,则天下万国之君臣百姓,尽是邪教之子孙。祖白之胆,信可包天矣!)其时略同,考之史册,推以历年,(试问祖白,此史册是中夏之史册乎?是如德亚之史册乎?如谓是中夏之史册,则一部《二十一史》,无有“如德亚天主教”六字;如谓是如德亚之史册,祖白中夏人何以得读如德亚之史?必祖白臣事彼国,输中国之情,尊如德亚为君,中夏为臣,故有“史册”、“历年”之论。不然,我东彼西,相距九万里,安有同文之史册哉!谋背本国,明从他国,应得何罪,请祖白自定。)在中国为伏羲,(谓我伏羲是天主教之子孙,岂非卖君作子,以父事邪教?祖白之头可斩也!)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远,为中国有人之始。(伏羲以前,有盘古、三皇、天皇氏已有干支。自天皇甲子至明天启癸亥,凡一千九百三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年,为天官家中积分历元。祖白历官不知历元之数,而谓伏羲以前中夏无人,岂止于惑世诬民已哉?斯天罔人之罪,祖白安所逃乎! )此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伏羲是如德亚之苗裔,则五帝三王以至今日之圣君圣师圣臣,皆令其认邪教作祖,置盘古三皇亲祖宗于何地?即寸斩祖白,岂足以尽其无君无父之罪 !以中夏之人而认西洋之邪教作祖,真杂种也。上天何故而生此人妖哉!)自西徂(cú)东,天学固其所怀来也。生长子孙,家传户习。此时此学之在中夏,必倍昌明于今之世矣。(伏羲时, 天主教之学既在我中夏家传户习,且倍昌明于今之世,若其书有存者,自有书契,至今绝无天主教之文。祖白无端倡此妖言,出自何典?不知祖白是何等心窍,国家有法必剖祖白之胸,探其心以视之!)延至唐虞,下迄三代,君臣告诫于朝,圣贤垂训于后,往往呼天称帝,以相警励。夫有所受之也,岂偶然哉!(以《二典》、《三谟》、《六经》、《四书》之天帝,为受之邪教之学,诬天非圣极已。即啖祖白之肉,寝祖白之皮,犹不c足以泄斯言之恨!)其见之《书》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引《书》九十五言。)《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引《诗》一百一十言。) 《鲁论》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引《论语》二十六言。)《中庸》曰:“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引《中庸》二十言。)《孟子》曰:“乐天者保天下。”(引《孟子》五十九言。)凡此诸文何,莫非天学之微言法语乎?(往时利玛窦引用中夏之圣经贤传,以文饰其邪教,今祖白径谓中夏之圣经贤传,是受邪教之法语微言。祖白之罪,可胜诛乎?!)审是,则中国之教,无先天学者。(无先天学,则先圣先贤皆邪教之后学矣。凡百君子读至此而不痛哭流涕与之共戴天者,必非人也!)
噫!小人而无忌惮,亦至此哉!不思我大清今日之天下,即三皇五帝之天下也;接三皇五帝之正统,大清之太祖、太宗、世祖、今上也;接周公孔子之道统(还有制统),大清之辅相师儒也。祖白谓历代之圣君圣臣,是邪教之苗裔,《六经》《四书》是邪教之微言,将何以分别我大清之君臣而不为邪教之苗裔乎?祖白之胆何大也!世祖碑天主教之文有曰;“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至于玄笈贝文所称《道德》《楞严》诸书,虽尝涉猎,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一)大哉圣谟,真千万世道统之正脉,后虽有圣人,弗能驾世祖斯文而上之也。盖祖白之心,大不满世祖之法尧舜,尊周孔,故著《天学传概》,以辟我世祖,而欲专显天主之教也。以臣抗君,岂非明背本国,明从他国乎?而弁其端者曰:“康熙三年,岁在甲辰春王正月,柱下史毗陵许之渐敬题。”
噫吁戏,异乎哉,许先生而为此耶!学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冯应京(二)、樊良枢者(三),若而人为天主教作序多矣,或序其历法,或序其仪器,或序其算数。至《进呈书像》一书(四),则罔有序之者,实汤若望自序之可见。徐、李诸人,犹知不敢公然得罪名教也。若望之为书也曰,“男女各一,以为人类之初祖”,未敢斥言覆载之内,尽是其教之子孙。君子直以妄目之而已矣。祖白之为书也,尽我大清而如德亚之矣,尽我大清及古先圣帝圣师圣臣而邪教苗裔之矣,尽我历代先圣之圣经贤传而邪教绪余之矣,岂止于妄而已哉!实欲挟大清之人,尽叛大清而从邪教,是率天下无君无父也!而先生序之曰:“二氏终其身于君臣父子,而莫识其所为天。即儒者,或不能无弊。”噫!是何言也!二氏供奉皇帝龙牌,是识君臣;经言“斋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二亲”,是识父子。况吾儒以五伦立教乎!唯天主耶稣谋反于其国,正法钉死,是莫识君臣;耶稣之母玛利亚,有夫名若瑟,而曰耶稣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得供奉祖父神主,是莫识父子。先生反以二氏之识君臣父子者,谓之为莫识君臣父子;以耶稣之莫识君臣父子者,谓之为识君臣父子。何剌谬也!儒者有弊,是先圣乎,先贤乎,后学乎?不妨明指其人,与众攻之。如无其人,不宜作此非圣之文,自毁周孔之教也。
杨墨之害道也,不过曰“为我”,“兼爱”,而孟子亟拒之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传概》之害道也,苗裔我群臣,学徒我周孔,祖白之意若曰,孔子之道不息,天主之教不著。孟子之拒,恐人至于无父无君;祖白之著,恐人至于有父有君。而先生为祖白作序,是拒孔孟矣,遵祖白矣!“儒者不能无弊”,先生自道之也。意者先生或非大清国之产乎,或非大清国之科目乎,胡为而为邪教序?此非圣之书,发此非圣之言也(六)。先生过矣!
寻复思之,是非先生之笔也。何以明之?先生读书知字,发身庠序为名进士,筮(shì)仕为名御史,其于圣人之道,幼学壮行,熟矣。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先王之所素定者也,肯屑为此非圣妖书之序哉!或者,彼邪教人之谋,以先生乃朝廷执法近臣,又有文名,得先生之序,以标斯书,使天下人咸曰,许侍御有序,则吾中夏人信为天主教之苗裔,勿疑矣。妖言惑众,有鱼腹天书之成效。故托先生之名为之序,既足以摇动天下人之心,更足为邪教之证据于将来也。必非先生之笔也。不然,或先生之门人、幕客,弗体先生敬慎名教之素心,假借先生之文以射自鸣钟等诸奇器,必非先生之笔也。再不然,近世应酬诗文,习为故套,有求者率令床头捉刀人给之,主者绝弗经心,不必见其文读其书哉?况先生戴星趋朝,出即入台治事,退食又接见贤士大夫,论议致君泽民之术,奚暇读其书哉?使先生诚得读其书,见我伏羲氏以至今日之君臣土庶,尽辱为邪教之子孙,《六经》《四书》尽辱为邪教之余论,当必发竖眦裂,掷而抵其书于地之不早,尚肯为之序乎?此光先之所以始终为必非先生之笔也。光先之《辟邪论》《距西集》杀青五六年矣,印行已五千余部,朝野多谬许之。而先生独若未之见,若未之闻,岂于非圣之书,反悦目乎?必不然矣!于此愈信必非先生之笔也。
虽然,光先能信必非先生之笔,有位君子能信必非先生之笔,天下学人能信必非先生之笔。但此序出未二月,业已传遍长安。非先生之笔,而先生不亟正之,恐后之人未必能如光先、能如今日之有位君子、能如今日之天下学人能信必非先生之笔也。得罪名教,虽有孝子慈孙,岂能为先生讳哉? 犹之,光先今日之呼吾家老不晓事也,先生当思所以处此矣。
天主耶稣谋反于如德亚国,事露正法,同二盗钉死十字架上,是与众弃之也,有若望之《进呈书像》可据。然则,天主耶稣者乃彼国之大贼首,其教必为彼国之厉禁,与中夏之白莲、闻香诸邪实同。在彼国则为大罪人,来我国则为大圣人,且谓我为彼教之苗裔而弗知辱;谓我为彼教之后学而弗知恶。使如德亚之主臣闻之,宁不嗤我中夏之士大夫无心知无目识乎?先生虽未尝为之序,而序实有先生之名,先生能晏然已乎?
以谋反之遗孽,行谋反之邪教,开堂于京师宣武门之内、东华门之东、阜城门之西,山东之济南,江南之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熟、上海,浙之杭州、金华、兰谿,闽之福州、建宁、延平、汀州,江右之南昌、建昌、赣州,东粤之广州,西粤之桂林,蜀之重庆、保宁,楚之武昌,秦之西安,晋之太原、绛州,豫之开封,凡三十窟穴。而广东之香山澳,盈万人盘踞,其间成一大都会,以暗地送往迎来。若望藉历法以藏身金门,而棋布邪教之党羽于大清京师十二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
明纲之所以不纽者,以废前王之法尔,律严通海泄漏,徐光启以历法荐利玛窦等于朝。以数万里不朝贡之人,来而弗识其所从来,去而弗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之,止不关防之,十五直省之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国人之政否?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遂成习矣。不察伏戎于莽,万一窃发,先生将用何术以谢此一序乎?《时宪历》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谓其暗窃正朔之尊以予西洋,而明白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具疏具呈争之。今谓伏羲是彼教之苗裔,《六经》是彼教之微言,而“依西洋新法”五字,岂非奉彼教正朔之实据明验乎?惑众之妖书已明刊印传播,策应之邪党已分布各省咽喉,结交士大夫以为羽翼,煽诱小人以为爪牙,收拾我天下之人心,从之者如水之就下。朝廷不知其故,群工畏势不言,养虎卧内,识者以为深忧。而先生不效贾生之痛哭,尚反为其作序以谀之乎!光先抱杞忧者六年矣,怀书君门,抑不得通,惟付之笔伐口诛,以冀有位者之上闻。先生乃圣门贤达,天子谏臣,不比光先之无官。守言责,执典章,以声罪致讨,实先生学术之所当尽、职分之所当为者,况有身后之累之一序乎?光先与先生素未谋面而辄敢以书唐突先生者,为天下古今万国君臣士庶之祖祢卫,为古先圣人之圣经贤传卫,为天下生灵将来之祸乱卫,非得已也。请先生速鸣攻之之鼓,以保立言之令名,以消身后之隐祸,斯光先之所以为先生计,非诮(qiào)让先生也。幸先生亟图之,知我罪我,惟先生所命。主臣主臣。
康熙甲辰(1664年) 三月二十五日,光先再顿首面投。
(一)此顺治十四年二月御制。在下文及本辑所收利、南等人著作中,各人都据自身需要,屡予援引,以断章取义。现将其中最主要部分,附录于下,后凡遇此,不再出注。文曰:“凡历之立法虽精,而后不能无修改,亦理势之必然也。自汉已还,讫于元末,修改者七十余次,创法者十有三家。至于明代,虽改元《授时历》为“大统”之名,而积分之术实仍其旧。洎(jì)乎晚季,分至渐乖,朝野之言,佥(qiān)云宜改。而西洋学者,雅善推步。于时汤若望航海而来,理数兼畅,被荐召试,设局授餐。奈众议纷纭,终莫能用。岁在甲甲,朕仰承天眷,诞受多方,适当正位凝命之时,首举治历明时之典。仲秋月朔,日有食之,特遣大臣,督率所司,登台测验。其时刻分秒起复方位,独与若望预奏者悉相符合。及乙酉孟春之望,再验月食,亦纤毫无爽。岂非天生斯人,以待朕创制立法之用哉?朕特任以司天,造成新历,敕名《时宪》,颁行远迩。若望素习泰西之教,不婚不宦,只承朕命,勉受卿秩,洊历三品,仍赐以“通玄教师”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职,都成宣武门内向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近复取锡赉所储,而更新之。朕巡幸南苑,偶经斯地,见神之仪貌,如其国人;堂牖(yǒu)器饰,如其国制。问其给上之书,则曰:此天主教之说也。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至于玄笈贝文所称《道德》《楞严》诸书,虽尝涉猎,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但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涓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已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赐额名曰“通玄佳境”,而为之计。”(见清黄伯禄《正教奉褒》,光绪甲午上海慈母堂重印本,页二九。)
(二)冯应京:字可大,号慕岗,安徽泗县人,万历年间名御史。事迹见《明史》本传。
(三)樊良枢:字尚植,号致虚,江西进贤人,万历进士。官至浙江副使,有《樊致虚诗集》。
(四)《进呈书像》:参见《邪教三图说评》
(五)见《孟子·媵文公下》
(六)“发”原作▪️,据清抄本补。
(七)《距西集》:存,笔者未见。台北中央图书馆善本部有藏本。
辟邪论上
圣人之,平实无奇,一涉高奇,即归怪异。杨墨之所以为异端者,以其持理之偏而不轨于中正,故为圣贤之所拒。矧(shěn)其人其学,不敢望杨墨之万一,而怪僻妄诞,莫与比伦。群谋不轨,以死于法,乃妄自以为冒覆宇宙之圣人,而欲以其道,教化于天下。万国不有,所以迸之,愚民易惑于邪,则遗祸将来定非渺小。此主持世道者,他日之忧也。故不惮繁冗,据其说以辟之。
明万历中,西洋人利玛窦与其徒汤若望、罗雅谷奉其所谓天主教,以来中夏(一)。其所事之像,名曰耶稣。手执一圆像,问为何物?则曰天。问天何以持于耶稣之手?则曰天不能自成其为天,如万有之不能自成其为万有,必有造之者而后成。天主为万有之初有,其有无元而为万有元,超形与声,不落见闻,乃从实无造成实有。不需材料、器具、时日。先造无量数天神无形之体,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汇诸物,以为覆载安养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飞走鳞介、种植等类。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亚当,女名厄袜,以为人类之初祖。天为有始,天主为无始,有始生于无始,故称天主焉。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灵魂;造地狱,以苦不事天主者之灵魂。人有罪应入地狱者,哀悔于耶稣之前,并祈耶稣之母以转达于天主,即赦其人之罪,灵魂亦得升于天堂。惟诸佛为魔鬼,在地狱中永不得出。问耶稣为谁,曰即天主。问天主主宰天地万物者也,何为下生人世?曰天主悯亚当造罪,祸延世世胤裔,许躬自降生救赎。于五千年中,或遣天神下告,或托前知之口代传降生在世事迹,预题其端,载之国史。降生期至,天神报童女玛利亚胎孕天主,玛利亚怡然允从,遂生子名曰耶稣。故玛利亚为天主之母,童身尚犹未坏。问耶稣生于何代何时?曰生于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
噫,荒唐不诞亦至此哉!夫天二气之所结撰而成,非有所造而成者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二)”时行而物生,二气之良能也。天设为天主之所造,则天亦块然无知之物矣,焉能生万有哉?天主虽神,实二气中之一气,以二气中之一气,而谓能造生万有之二气,于理通乎?无始之名,窃吾儒无极而生太极之说。无极生太极,言理而不言事;苟以事言,则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论则涉于诞矣。夫子之“不语怪力乱神”,正为此也。而所谓无始者,无其始也。有无始,则必有生无始者之无无始;有生无始者之无无始,则必又有生无无始者之无无无始。溯而上之,曷有穷极?而无始亦不得名天主矣。误以无始为天主,则天主属无而不得言有。真以耶稣为天主,则天主亦人中之人,更不得名天主也。设天果有天主,则覆载之内四海万国无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无独主如德亚一国之理。独主一国,岂得称天主哉!既称天主,则天上地下四海万国物类甚多,皆待天主宰制。天主下生三十三年,谁代主宰其事?天地既无主宰,则天亦不运行,地亦不长养,人亦不生死,物亦不蕃茂,而万类不几息乎? 天主欲救亚当,胡不下生于造天之初,乃生于汉之元寿庚申?元寿庚申距今上顺治己亥,才一千六百六十年尔。而开辟甲子至明天启癸亥以暨于今,合计一千九百三十七万九千四百九十六年。此黄帝《太乙》所记。从来之历元,非无根据之说。太古洪荒都不具论,而天皇氏有干支之名,伏羲纪元癸未,则伏羲以前已有甲子明矣。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而尧以甲辰纪元。尧甲辰距汉哀庚申,计二千三百五十七年。若耶稣即是天主,则汉哀以前尽是无天之世界,第不知尧之钦若者何事,舜之察齐者何物也;若天主即是耶稣,孰抱持之而内于玛利亚之腹中?齐谐之志怪,未有若此之无稽也!
男女媾精,万物化生,人道之常经也。有父有母,人子不失之辱,有母无父,人子反失之荣。四生中湿生无父(三),母胎卵化,俱有父母。有母而无父,恐不可以为训于彼国,况可闻之天下万国乎!世间惟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想彼教尽不知父乎?不然,何奉无父之鬼如此其尊也!尊无父之子为圣人,实为无夫之女开一方便法门矣。玛利亚即生耶稣,更不当言童身未坏,而孕胎何事,岂童女怡然之所允从?且童身不童身谁实验之?《礼》 “内言不出”(四)、“公庭不言归女”(五),所以明耻也。母之童身,即禽兽不忍出诸口,而号为圣人者反忍出诸口,而其徒反忍鸣之天下万国乎?耶稣之师弟,禽兽之不若矣!“童身”二字,本以饰无父之嫌,不知欲盖而弥彰也。
天堂地狱,释氏以神道设教,劝怵愚夫愚妇,非真有天堂地狱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百祥百殃,即现世之天堂地狱。而彼教则凿然有天堂地狱在于上下,奉之者升之天堂,不奉之者堕之地狱。诚然,则天主乃一邀人媚事之小人尔,奚堪主宰天地哉!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恶人,犹可言也;苟奉者皆恶人,不奉者皆善人,抑将颠倒善恶而不恤乎?释氏之忏悔,即颜子“不二过”之学,未尝言罪尽消也。而彼教则哀求耶稣之母子,即赦其罪而升之于天堂。是奸盗诈伪皆可以为天人,而天堂实一大逋逃薮(sǒu)矣。拾释氏之唾余,而谓佛堕地狱中永不得出,无非满腔忌嫉,以腾妒妇之口。如真为世道计,则著至大至正之论,如吾夫子正心诚意之学,以修身齐家为体,治国平天下为用,不期人尊而人自尊之。奈何辟释氏之非,而自树妖邪之教也?
其最不经者,未降生前将降生事迹预载国史。夫史以传信也,安有史而书天神下告未来之事者哉?从来妖人之惑众,不有所藉托,不足以倾愚之心,如社火狐鸣、鱼腹天书、石人一眼之类而曰史者,愚民不识真伪,咸曰信真天主也。非然,何国史先载之耶?观盖“法氏之见耶稣频行灵迹,人心翕(xī)从,其忌益甚”之语,则知耶稣之聚众谋为不轨矣。官忌而民言发,非反而何?耶稣知不能免,恐城中信从者多,尽被拘执,傍晚出城入山囿中,跪祷被执之后,众加耶稣以僭王之耻,取王者绛色敝衣披之,织刚刺为冕,以加其首,且重击之。又纳杖于耶稣之手,比之执权者焉。伪为跪拜,以恣戏侮。审判官比辣多计释之而不可得,姑听众挞以泄恨。全体伤剥,卒钉死于十字架上。观此,则耶稣为谋反之渠魁,事露正法明矣。而其徒邪心未革,故为三日复生之说,以愚彼国之愚民。不谓中夏之人竟不察其事之有无、理之邪正,而亦信之皈之。其愚抑更甚也。
夫人心翕从,聚众之迹也;被人首告,机事之败也;知难之至,无所逃罪也;恐众被拘,多口之供也;傍晚出城,乘天之黑也;入山囿中,逃形之深也;跪祷于天,祈神之佑也;被以王者之衮冕,戏遂其平日之愿也;伪为跪拜,戏其今日得为王也;众挞泄恨,泄其惑人之恨也;钉死十字架上,正国法快人心也。其徒讳言谋反,而谋反之真赃实迹,无一不自供招于《进呈书像说》中。十字架上之钉死,正现世之剑,树地狱而云佛在地狱,何所据哉?且十字架何物也?以中夏之刑具考之,实凌迟重犯之木驴子尔。皈彼教者,令门上、堂中俱供十字架。是耶稣之弟子无家不供数木驴子矣,其可乎?
天主造人,当造盛德至善之人,以为人类之初祖,犹恐后人之不善继述。何造一骄傲为恶之亚当,致子孙世世受祸?是造人之人贻谋先不臧矣。天主下生救之,宜兴礼乐,行仁义,以登天下之人于春台,其或庶几;乃不识其大而好行小惠,惟以瘳(chōu)人之疾、生人之死、履海幻食、天堂地狱为事,不但不能救其云礽,而身且陷于大戮,造天之主如是哉!及事败之后,不安义命,跪祷于天,而妖人之真形,不觉毕露。夫跪祷祷于天也,天上之神孰有尊于天主者哉?孰敢受其跪,孰敢受其祷?以天主而跪祷,则必非天主明矣。按耶稣之钉死,实壬辰岁三月二十二日,而云天地人物俱证其为天主:天则望日食既,下界大暗;地则万国震动。夫天无二日,望日食既,下界大暗,则天下万国宜无一国不共睹者。日有食之,《春秋》必书,况望日之食乎?考之汉史,光武建武八年壬辰四月十五日无日食之异,岂非天丑妖人之恶,使之自造一谎,以自证其谎乎?连篇累牍,辩驳其非,总弗若耶稣跪祷于天,则知耶稣之非天主痛快斩截,真为照妖之神镜也。一语允堪破的,则必俟(sì)数千言者。盖其刊布之书,多窃中夏之语言文字,曲文其妖邪之说,无非彼教金多,不难招致中夏不得志之人而代为之创润,使后之人第见其粉饰之诸书,不见其原来之邪本,茹其华而不知其实,误落彼云雾之中,而陷身于不义,故不得不反复辨论,以直捣其中坚。世有观耶稣教书之君子,先览其《进呈书像》及《蒙引》(六)、《日课》三书(七),后虽有千经万论,必不屑一寓目矣。邪教之妖书妖言,君子自能辦之,而世有不知之无状,真有不与同中国者。试举以告夫天下之学人焉。今日之天主堂,即当年之首善书院也。若望乘魏珰之焰,夺而有之,毁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木主,践于粪秽之内(八),言之能不令人眦欲裂乎?此司马冯元飚(biāo)之所以切齿痛心,向人涕泣而不共戴天者也(九)。读孔氏书者,可毋一动念哉?邪说鼓行,惧其日滋,不有圣人何能止息?孟子之拒杨墨,恶其充塞仁义也,天主之教岂特充塞仁义已哉?禹平水土,功在万世,先儒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其拒杨墨也。兹欲拒耶稣,息邪教,正人心,塞乱源,不能不仰望于主持世道之圣人云。韩愈有言:“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吾于耶稣之教亦然。
时顺治己亥(1659年) 仲夏望日,新安布衣杨光先长公氏著。
(一)此说有误。汤、罗入华不是万历中,而是天启初年。
(二)见《论语·阳货》
(三)四生:指卵生、胎生、湿生和纪生。是印度的一种分类法。见《阿毗达摩俱舍论》。
(四)“内言不出”:原文作“内言不出于梱”。见《礼记·典礼上》
(五)见《礼记·典礼下》
(六)《蒙引》:全名《天学蒙引》。署“西海何大化,古吴周志于道甫著”,是部天主教启蒙教材。
(七)《日课》:全名《圣教日课》。龙华民译著,是部天主教日常公诵的经本。
(八)杨氏此摘不实,方豪先生曾有辨证。见本书附录一:方豪《不得已序》。
(九)冯元飈:字尔tao(弢),慈溪人,天启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明史》卷二五七有传。杨氏此说,应是有意篡改事实:冯氏切齿痛心的对象为阉党。
辟邪论中
圣人学问之极功,只一穷理以几于道,不能于理之外又穿凿一理,以为高也。故其言中正平常,不为高远奇特之论。学人终世法之,终世不能及焉。此中庸之所以鲜能也。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恃其给捷之口,便佞之才,不识推原事物之理、性情之正,惟以辩博为圣,瑰异为贤。罔恤悖理叛道,割裂坟典之文而支离之。譬如猩猩鹦鹉,虽能人言,然实不免其为禽兽也。利玛窦欲尊耶稣为天主,首出于万国圣人之上而最尊之,历引中夏《六经》之上帝,而断章以证其为天主。曰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之上帝,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也。苍苍之天,乃上帝之所以役使者,或东或西,无头无腹,无手无足,未可为尊;况于下地乃众足之所踏践,污秽之所归,安有可尊之势?是天地皆不足尊矣。如斯立论,岂非能人言之禽兽哉!
夫天,万事万物万理之大宗也。理立而气具焉,气具而数生焉,数生而象形焉。天为有形之理,理为无形之天,形极而理见焉,此天之所以即理也。天函万事万物,理亦函万事万物,故推原太极者,惟言理焉,理之外更无所谓理,即天之外更无所谓天也。《易》之为书,言理之书也,理气数象备焉。乾之卦“乾:元亨利贞”,彖(tuàn)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夫元者理也,资始万物,资理以为气之始,资气以为数之始,资数以为象之始,象形而理自见焉,故曰“乃统天”。《程传》(一)“乾,天也,专言之则道也,分言之,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此分合之说,未当主于分,而不言合也。专者体也,分者用也。言分之用而专之体自在矣。天主教之论议行为纯乎功用,实程子之所谓鬼神,何得擅言主宰?朱子云“乾元是天之性,如人之精神。”(二)岂可谓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神耶?观此,则天不可言自是天,帝不可言自是帝也。万物所尊者惟天,人所尊者惟帝。人举头见天,故以上帝称天焉;非天之上又有一帝也。《书》云“钦若昊天,惟天降灾祥在德与天叙、天秩、天命、天讨”(三)。《诗》云“畏天之威”(四),“天鉴在兹”(五),皆言天也。“上帝是皇”(六),“昭事上帝”(七),言敬天也。“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八)言不敢逆天也。“惟皇上帝,降衷下民。”(九)衷者,理也,言天赋民以理也。《礼》云“天子亲耕,粢(zī)盛秬(jù)鬯(chàng),以事上帝。”(十)言顺天时重农事也。凡此皆称上帝,以尊天也,非天自天,而上帝自上帝也。读书者毋以辞害意焉。今谓天为上帝之役使,不识古先圣人何以称人君为天子,而以役使之贱比之为君之父哉?以父人君之天,为役使之贱,无怪乎令皈其教者,必毁天地君亲师之牌位而不供奉也。不尊天地,以其无头腹手足,踏践污秽而践之也;不尊君,以其为役使者之子而轻之也;不尊亲,以耶稣之无父也。天地君亲尚如此,又何有于师哉!此宣圣木主之所以遭其毁也。乾坤俱汨,五伦尽废,非天主教之圣人学问断不至此!宜其夸诩,自西徂东,诸大邦国咸习守之,而非一人一家一国之道也。吁嘻,异乎哉,自有天地以来,未闻圣人而率天下之人于无父无君者也!诸大邦国苟闻此道,则诸大邦国皆禽兽矣,而况习守之哉!
夫不尊天地而尊上帝,犹可言也;尊耶稣为上帝,则不可言也。极而至于尊凡民为圣人,为上帝,犹可言也;胡遽至于尊正法之罪犯为圣人,为上帝,则不可言也。古今有圣人而正法者否?上帝而正法,吾未之前闻也。所谓天主者,主宰天地万物者也;能主宰天地万物,而不能主宰一身之考终, 则天主之为上帝可知矣?彼教诸书于耶稣之正法,不言其钉死者何事,第云救世功毕,复升归天。其于圣人易箦之大事,亦太草草矣!夫吾所谓功者,一言而泽被苍生,一事而恩施万世,若稷之播百谷,契之明人伦,大禹之平水土,周公之制礼乐,孔子之法尧、舜,孟子之拒杨墨,斯救世之功也。耶稣有一于是乎?如以瘳人之病,生人之死为功,此大幻术者之事,非主宰天地万物者之事也。苟以此为功,则何如不令人病,不令人死,其功不更大哉?夫既主宰人病人死,忽又主宰人瘳人生,其无主宰已甚,尚安敢言功乎?故只以“救世功毕,复升归天”八字结之,绝不言毕者何功,功者何救。盖亦自知其辞之难措,而不觉其笔之难下也。以正法之钉死,而云“救世功毕,复升归天”,则凡世间凌迟、斩、绞之重犯,皆可援此八字,为绝妙好辞之行状矣。妖书妖言,悖理反道,岂可一日容于中夏哉!
(一)《程传》:指《周易》程颐传。
(二)见《周易本义》。
(三)《尚书》无此语,疑非原引。
(四)见《周颂·我将》
(五)《诗经》无此语,疑错引。
(六)见《周颂·执竟》
(七)见《大雅·大明》
(八)此非《诗经》句,见《尚书·汤誓》
(九)此非《诗经》句,见《尚书·汤诰》。又,原文作“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辟邪论下
详阅利玛窦阐明天主教诸书之论议,实西域七十二种旁门之下,九十六种邪魔之一。其诋毁释氏欲驾而上之,此其恒情,原不足为轻重。利玛窦之来中夏并老氏而排之。士君子见其排斥二氏也,以为吾儒之流亚,故交赞之,援引之,竟忘其议论之邪僻,而不觉其教之为邪魔也。且其书止载耶稣“救世功毕,复升归天”,而不言其死于法。故举世缙绅,皆为其欺蔽。此利玛窦之所以为大奸也。其徒汤若望之知识卑暗于利玛窦,乃将耶稣之情事于《进呈书像》中和盘托出,予始得即其书以辟之。岂有彼国正法之罪犯而来中夏为造天之圣人,其孩孺我中夏人为何如也!耶稣得为圣人,则汉之黄巾、明之白莲皆可称圣人矣!耶稣既钉死十字架上,则其教必为彼国之所禁;以彼国所禁之教,而欲行之中夏,是行其所犯之恶矣,其衷讵(jù)可测哉!若望之流,开堂于江宁、钱塘、闽、粵,实繁,有徒呼朋引类,往来海上,天下之人知爱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干禁,是爱虎豹之纹皮,而豢之卧榻之内,忘其能噬人矣。
夫国之有封疆,关之有盘诘,所以防外伺杜内泄也。无国不然。今禁令不立,而西洋人之集中夏者,行不知其遵水遵陆,止不知其所作所为,惟以精工奇巧之器,鼓动士大夫,天堂地狱之说,煽惑我愚民。凡皈之者,必令粘一十字架于门上,安知其非左道之暗号乎?世方以其器之精巧而爱之,吾正以其器之精巧而惧之也。输之攻墨之守,岂拙人之所能哉?非我族类,其心必殊,不谋为不轨于彼国,我亦不可弛其防范;况曾为不轨于彼国乎?兹满汉一家,蒙古国戚,出入关隘,犹凭符信以行,而西洋人之往来,反得自如而无讥察,吾不敢以为政体之是也。正人必不奉邪教,而奉邪教者必非正人,以不正之人行不正之教,居于内地为国显官,国之情势保毋不外输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谋国君子毋以其亲昵而玩视之也。彼教之大规,行教之人则不婚不宦。考汤若望之不婚,则比顽童矣;不宦则通政使食正二品、服俸加二级,掌钦天监印矣。行教而叛教,业已不守彼国之法,安能必其守大清之法哉?《诗》云“相彼雨雪,先集维霰。”(一)“依西洋新法”五字,不可谓非先集之霰也。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识者犹恶其眼,予盖恶其眼云。怀书君门,抑不得达,故著斯论,以表天主教之隐祸有如此。宁使今日詈予为妒妇,不可他日神予为前知也。
《论》甫刻成,客有向予言,利玛窦于万历时,阴召其徒以贸易为名,舳(zhú)舻衔尾,集广东之香山澳中,建城一十六座。守臣惧,请设香山参将,增兵以资弹压。然彼众日多,渐不可制(二)。天启中,台省始以为言,降严旨,抚臣何士晋廉洁刚果,督全粵兵毁其城(三),驱其众,二、三十年之祸一旦尽消,此往事之可鉴也。今若望请召彼教人来治历,得毋借题为复踞澳之端乎?彼国距中夏十万里,往返必须十年,而三月即至,是不在彼国而在中国明矣。不知其人于何年奉何旨安插何地方也?如无旨安插,则私越之干禁,有官守言责之大君子,可无半语一诘之哉?兹海氛未靖,讥察当严。庙堂之上,宜周毖(bì)饬之画,毋更揖盗自诒后日之忧也。续因所闻,补赘论末,忧国大君子鉴之。
(一)见《小雅·頍(kuǐ)弁》。又,原文作“如彼雨雪,先集维霰”。
(二)设香山参将事,《明熹宗实录》卷一有载:“万历四十二年,始设参将于中路雍陌营,调千人守之。”而澳门有西洋人居,与利玛窦来华无关。
(三)“毁城”事,他文献所载与此有出入。如《明熹宗实录》卷五十八云:“总督两广何士晋报濠境澳夷,迩来盘踞披猖,一时文武各官决策防御。今内奸绝济,外夷畏服,愿自毁其城,止留海滨一面,以御红夷。”
邪教三图说评(一)(临汤若望进呈图像说)
上许先生书后,追悔著《辟邪论》时,未将汤若望刻印“国人拥戴耶稣”及“国法钉死耶稣”之图像刊附论首,俾天下人尽见耶稣之死于典刑,不但土大夫不肯为其作序,即小人亦不屑归其教矣。若望之《进呈书像》共书六十四张,为图四十有八。一图系一说于左方。兹弗克具载,止摹“拥戴耶稣”及“钉架”、“立架”三图三说,与天下共见耶稣乃谋反正法之贼首,非安分守法之良民也。(图说附于左方。)
(汤若望曰,耶稣出行教久,知难期之渐迫也,旋反都城就之。从来徒行,惟此入都,则跨一驴,且都人望耶稣如渴,闻其至也,无贵贱大小,倾城出迎。贵者缙绅,贱者百姓,拥戴之盛,取死之速,妖人从来如此。)有以衣覆地弗使驴足沾尘者,有折枝拥导者,(如此拥戴耶稣,则如德亚国主与耶稣势不能两立矣。非国主杀耶稣,则耶稣必弑国主。)前后左右群赞其为天主无间也。噫!是盖有二意焉:一少显尊贵之相,(妖人之情不觉自露,惟其尊贵所以取钉死。)于受难之前,以见受难实为天主;一借此重责五日后有变心附恶者。(五日前奉迎者,愚民受其惑;五日后变心者,惧王法悔前非也。)若曰尔所随声附恶,以相倾陷者,非即尔前日欢迎入城赞为天主者乎!(自供。)杨子曰:此汤若望自招天主耶稣是谋反之口供。
若望曰,其钉十字架也,左右手各一钉,二足共一钉。有二盗在狱未决者,今亦取出钉之,以等耶稣于盜,为大辱云。杨子曰,犯人画招已毕,此真所谓不刑而招。
若望曰,钉毕,则立其架,中耶稣两傍盗也。耶稣悬架,天地人物俱证其为天主:天证,如太阳当望而食,法所不载,且全食下界大暗,且久食历时十二刻也;地证,全地皆震,惊动万国;人证,无数死者离墓复活;物证,如石块自破,帷帐自裂等是也。尤足异者,既终之后,恶众有眇一目者举枪刺耶稣肋,以试其实死与否,刺血下注,点及恶目,随与复明。(邪教之意,恐人议论耶稣是邪教,不是天主下生,故引天地人物作证,以见耶稣真是天主,必要说到理事之所,无使人不敢不信。细考耶稣钉死之日,依西历乃三月之十六日,考之中历为汉光武建武八年壬辰岁之三月二十二日。夫天既肯违常度,非朔日而食以证耶稣为天主,何不食于廿二而食于十六?若望亦自知下弦之月,不能全掩太阳之光,故于既望月圆之朝,疾行一百八十二度半,以食日,下界大暗。精于历法如若望,方知此食在,羲和历官断断不能言,断断不敢言也。若望既敢妄言,吾亦姑以妄信。日有食之,《春秋》必书。但查建武八年三月、四月,无日食、地震之文,况望日日食乎?彼邪教人止知说燥脾之谎,以惑愚夫愚妇,不提防明眼学人有史册可考(二),以镜其失枝脱节也。独怪向来士大夫愿为定交,愿为援引,愿为作序,岂真无目,不过利其数件奇巧器物与之狎尔。殊不知一与亲昵,即弗能守自己之正学,乃玩物以徇人,举世尤而效之,遂遗天下后世无穷之祸。作俑无后,吾必以徐光启为万世大罪人之魁。)杨子曰:右三图三说是圣人,是反贼,是崇奉,是正法,吾弗能知,请历来作序先生辨之。
(一)此原作“临汤若望进呈图像说”,与前目录不合,今改。
(二)“提”原作“堤”。
正国体呈稿
江南徽州府新安卫官生编歙县民杨光先呈,为大国无奉小国正朔之理,一法无有闰有不闰之月,事关国体,义难缄默,请乞题参,会勘改正,以尊大国名分,以光一代大典事。
窃惟正名定分,在只字之间,成岁闰余有不易之法。顾法不可以紊乱,而名不可以假人。名以假人将召不臣之侮,法而紊乱定贻后世之讥。斯国体之攸关,非寻常之得失也。皇上乘乾御宇,抚有万国。从来幅员之广,重译之献,未有如皇上之盛者。而正朔之颁,实万国之所瞻听,后世之所效则,非一代因革损益之庶政比也,必名足以统万国,而法足以宪万世,始克称一代历焉。兹钦天监监正汤若望之以新法推《时宪历》也,于名则有无将之诛,于法则有扰纪之罪。为皇上之臣民者,岂能晏然而已乎?
夫《时宪历》者,大清之历,非西洋之历也;钦若之官,大清之官,非西洋之官也。以大清之官,治大清之历,其于历面之上宜书“奏准印造时宪历日”,颁行天下,始为尊皇上而大一统。今书上传“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其罪岂止无将已乎!《春秋》,鲁记事之史也;仲尼,鲁之老臣也。鲁臣而修鲁史,尚不敢自大其君,而必系之以“春王正月”。盖所以尊周天王而大一统,非藉周天王而张大夫鲁也。今以大清之历而大书“依西洋新法”,不知其欲共天王谁乎?如天王皇上,则不当书“依西洋新法”;敢书“依西洋新法”,是藉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实欲天王西洋,而鲁大清也。罪不容于诛矣!孔子惜繁缨,谓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今假以依西洋新法,此实见之行事,非托之空言者也,岂特繁缨已哉!若望必曰五字出自上传。夫上传者,传用其法,未尝传其特书五字于历面也。皇上即传其特书五字于历面,若望亦当引分以辞曰:冠履有定分,臣偏方小国之法,曷敢云大国“依”之而特书于历面以示天下万国,臣不敢也。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敢贪天子之命毋下拜不可师以辞乎(一)?如曰习矣,而不察小国命大国非习而不察之事也。人臣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雀。光先于本年五月内,曾具疏纠正疏,虽不得上达,而大义已彰于天下(二)。若望即当检举改正,以赎不臣之罪,何敢于十八年历日犹然大书五字?可谓怙(hù)终极矣!此盗窃名器之罪,一也。
三岁一闰,气盈朔虚之数也。无法以推之,何以知其某月当置闰,其月不当置闰乎?一月之内有一节气一中气,此常月之法也,有一节气而无中气,则以上半月为前月之中气,下半月为后月之节气,此置闰之法,夫人尽知也。新法于十八年闰七月十四日酉时正初刻交白露。八月节十四日以前作七月用,十四日以后作八月用。此有节气而无中气之为闰,此法之正也。忽又于十二月十五日申时正三刻,交立春正月节。此月有节气而无中气,正与闰七月之法同。是一岁而有两闰月之法矣。同一法也,而有闰有不闰,何以杜天下后世之口乎?且顺治十八年实闰十月,而新法谬闰七月,此不知其凭何理以推也?若望必曰西洋新法与羲和不同。夫用新法者,冀其精密于羲和之法也。而新法谬乱若此,不敢望羲和之万一,尚可侈口言《新法》哉!非特此也,一月有三节气,则又更异于有闰有不闰之法矣。至于冬至之刻至立春之刻,应有四十五日八时弱,而新法止四十四日一时三刻。将立春之刻趱(zǎn)在前一日六时三刻,是不应立春之日而立春,应立春之日而不立春。凡此开辟至今所未闻之法也。夫春为一岁之首,《礼经:月令》,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关于典礼何等重大,乃以偏方之新法,淆乱上国之《礼经》,亵天帝而慢天子,莫此为甚焉!《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三)新法之干于《政典》多矣。此俶(chù)扰天纪之罪,二也。
夫以堂堂之天朝,举一代之大经大法委之无将扰纪之人,而听其盗窃紊乱,何以垂之天下后世哉!总之,西洋之学,左道之学也。其所著之书,所行之事,靡不悖理叛道。世尽以其为远人也而忽之,又以其器具之精巧也而昵之。故若望得藉其新法,以隐于金门,以行邪教。久之,党与炽盛,或有如天主耶稣谋为不轨于其本国,与利玛窦谋袭日本之事,不几养虎自贻患哉。二事一见于若望进呈之书,一闻于海舶商人之口。如斯情事,君之与相,不可不一聆于耳中,以知天主教人之狼子野心,谋夺人国,是其天性。今呼朋引类,外集广澳,内官帝掖,不可无蜂虿(chài)之防,此光先之所以著《摘谬十论》以正其谬历,《辟邪三论》以破其左道也。谬历正而左道祛,左道祛而祸本亡,斯有位者之事也。伏乞详察备呈。事关国体,具疏题参,请敕满汉内各阁翰林六部九卿科道公同勘议,请旨改正,并将邪教迸斥,以为无将扰纪之戒。庶名分定而上国尊,历法正而大典光矣。字多逾格,仰祈鉴宥。为此具呈,须知,呈者。
顺治十七年(1643年) 十二月初三日具投,礼科未准。
(一)典出《国语·齐》:“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尔无下拜。”小白,齐桓公名。
(二)此疏《不得已》未收,其内容或与《正国体呈稿》同。
(三)见《尚书·胤征》。
中星说
古今掌故,无载籍可考,则纷如聚讼,终无足征。可以逞其私智,肆其邪说,以簧鼓天下后世,而莫之所经正。夫既有载籍可考,又有一定掌故,乃尽以为不可据,是先王之法不足遵,而载籍不足凭也。载籍以羲画为祖,然有画而无文,《尚书》有文有事,典雅足征。故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诚文章政事之祖。而又经历代大儒之所论注,则其为宪万世不待言矣。《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之后,即分命申命二氏,宅于四极, 考正星房虚昴四正之中星,此二氏必羲后之裔。与其司天之史守其家学,故世其官,而掌故之渊源必本之肇造。干支之太古学有师承,其来旧矣,定非创自胸臆,若今人之以“新”鸣也。考其四正之中星,咸以太阳之宿居于四正宫之中。盖太阳者,人君之象,中立而弗偏倚者也。人君宅中,以治天下,故以太阳宅于四正宫之中以象之,非无所取义而云然也。故星日鸟宿列于午宫之中。典曰:“日中星鸟。”(午宫正中之线,当星宿五度九十二分一十二秒三十七微五十纤。)房日兔宿,列于卯宫之中。典曰:“日永星火。”(卯宫正中之线,当房宿初度三分五十六秒一十二微五十纤。)虛日鼠宿,列于子宫之中。典曰:“宵中星虚。”(子宫正中之线,当虚宿五度九十九分九十九秒八十七微五十纤。)昴日鸡宿,列于酉宫之中。典曰:“日短星昴。”(酉宫正中之线,当昴宿三度二十五分六十八秒六十二微五十纤。)此《尧典》之所记载,历代遵守四千余年,莫之或议,可云不足法乎?
今西洋人汤若望尽更羲和之掌故而废黜之。将帝典真不足据,则世间载籍当尽付之祖龙一火矣。奚必存此赘疣,以为挠乱新法之具哉?
孔子之所以为圣人者,以其祖述尧舜也。考其祖述之绩,实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而已。圣而至于孔子,无以复加矣。而羲和订正星房虚昴之中星,乃《尧典》之所记载,孔子之所祖述。若望一旦革而易之,是尧舜载籍之谬,孔子祖述之非,若望是而孔子非,孔子将不得为圣人乎?试问举世之先知、后知、先觉、后觉,尧舜应祖述乎,不应祖述乎?必有能辨之者。如应祖述,则羲和之法,恐不可尽废也。予不惧羲和之学绝而不传,惧载籍之祖之掌故不能取信于今日,使后之学者,疑先圣先贤之典册尽为欺世之文具,而学脉道脉,从斯替矣。此予之所以大忧也。故于中星之辩,刺刺不休,以当贾生之痛哭,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礼·王制》曰:“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不以听作记者,其前知有今日乎?
选择议
窃惟阴阳五行之理,惟视生克制化之用,用得其理,则凶可化为吉;用违其理,则吉反变为凶。而斟酌权宜,非读书明理之人不能也。今天文、地理、时令三家,多是不读书之人藉此以为衣食之资。其于阴阳五行之理,原未融会贯通,以讹传讹,满口妄诞,究至祸人之事恒多,而福人之事恒少。
夫山有山之方位,命有命之五行,岁月有岁月之生死,详载《通书》。待人随理而变通之,故名其书曰“通”。通者,有变通之义。今庸术不能明理而变通之,反将变通之书,以文其不通之术,鲜有不误人也者。凡阴阳二宅,以其人之本命为主,山向岁月,俱要生扶本命,最忌克命。选择造命之理,要生扶之四柱,忌克泄之四柱。或三方不利,用事难缓,则用制杀化杀之《月令》,以化凶为吉;若《月令》生杀党杀,日时不良,则有凶而无吉。
如荣亲王之命,丁酉年生(一),纳音属火,以水为杀,宜选二木生旺之月以生火,令水不克火而生木,此化难生恩之法也。忌水生旺之月以克火,忌金生旺之月以生杀,此定理也。查戊戌年寅午戌三合火局,以北方为三杀,亥为劫杀,壬为伏兵,子为灾杀,癸为大祸,丑为岁杀。盖亥壬子癸,为阴阳二水临官帝旺之地,以水能灭火也。一说亥子丑为阴阳二火,墓绝之乡火,至北方而无气,其义与水克火同。此北方所以为寅午戌三合年之三杀也。又查《山家变运》(二),子午二山正五行属水,水墓在辰。戊戌年,遁得丙辰墓运纳音属土,选用公月月建,辛酉为庚金帝旺之乡,辛金临官之地,用官旺之金,生水以克火,加之墓运属土,母顾子而不克水,反助金以生水。查壬辰日干头透水,又纳音属水,众杀党聚,以克王命,何忌如之。且八月二十七日,实犯地空,《通书》忌理葬,岂汤若望未之见也?查甲辰时,奇门法犯伏吟。《经》云:“课中伏吟为最凶,天蓬加着地天蓬。天蓬若到天英生,须知即是反吟宫。八门反伏皆如此,生在生兮死在死。假令吉宿得奇门,万事皆凶不堪使。”荣亲王之葬年犯三杀:月犯生杀,日犯党杀,时犯伏吟。四柱无一吉者,不知其凭何书何理而选之也。幸用之以葬数月之王,若用之宦庶之家,其凶祸不可言矣!
(一)荣亲王:顺治幼子。生于顺治十四年(丁酉,一六五七)十月,十五年正月薨。
(二)《山家变运》:古方士书。
摘谬十论
一谬不用诸科较正之新
从来治历,以数推之,以象测之,以漏考之,以气验之。盖推算者,主数而不主象,恐推算与天象不合,故用回回科之太阴五星凌犯以较之;又恐推算、凌犯二家与天象不合,故用天文科台官之测验以考之。三科之较正精矣、当矣,而犹曰此数象之事,非气候时刻分秒事也,故用漏刻科考订。一日百刻之漏,布律管于候气之室,验葭灰飞之时刻分秒,以知推算之时刻分秒与天地之节气合与不合。此四科分设之意,从古已然。今惟凭一已之推算,竟废古制之诸科:禁回回科之凌犯,而不许之进呈,进自著之凌犯,以掩其推算之失。置天文科之台官,而不使之报象,废漏刻科之律管,而不考其飞灰。纵气候违于室中,行度舛于天上,谁则敢言?此若望所以能尽聋聩一世之人,得成其为新法也。
二谬 一月有三节气之新
按历法每月一节气,一中气,此定法也,亦定理也。顺治三年十一月大,癸卯。初一日癸卯卯初一刻大雪,十一月节。十五日丁巳亥正初刻冬至,十一月节。三十日壬申未初一刻小寒,十二月节。此是一月之内有两月之节气矣。自开天辟地至今,未闻有此法也。
三谬二至二分长短之新
按,至分之数,时刻均齐,无长短不一之差。冬至至夏至,古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时半弱,新法,一百八十二日二时;夏至至冬至,古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时半弱,新法一百八十三日一时弱。是夏至至冬至长十一时,而冬至至夏至短十一时矣。春分至秋分,古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时半弱,新法一百八十六日九时二刻十分弱;秋分至春分,古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时半弱,新法一百七十八日五时刻五分。是春分至秋分多八日三时五刻五分,而秋分至春分少八日三时五刻五分矣。
四谬夏至太阳行迟之新
太阳之行,原无迟疾,一昼夜实行一度。夏至太阳躔(chán)申宫参八度,参八出寅宫入戌宫,昼行地上度二百一十九度弱,故昼长;夜行地下度一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苟因夏至之昼长,而谓太阳之行迟,则夏至之夜短,太阳应行疾矣。迟于昼,而疾于夜,有是理乎?冬至太阳躔寅宫箕三度,箕三出辰宫入申宫,昼行地上度一百四十六度强,故昼短;夜行地下度二百一十九度弱,故夜长。苟因冬至之昼短而谓太阳之行疾,则冬至之夜长太阳应行迟矣。疾于昼而迟于夜,有是理乎?新法以夏至太阳之行迟,故将立秋压在后一日三时;以冬至太阳之行疾,故将立春攒在前一日六时。立夏立冬莫不皆差一日七八时,总因不明太阳之行,误之也。《礼经》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关于典礼,何等重大。兹以偏邦之新法,淆乱上国之礼经,慢天帝而亵天子,莫此为甚焉!
五谬移寅宫箕三度入丑宫之新
查寅宫宿度,自尾二度入寅宫起,(尾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七;箕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五十九分;斗初一、二、三、四度。)始入丑宫。今冬至之太阳实躔寅宫之箕三度,而新法则移箕三入丑宫,是将天体移动十一度矣。一宫移动,十二宫无不移动也。
六谬更调觜参二宿之新
四主七宿,俱以木金土日月火水为次序:南方七宿,井(木犴(àn))、 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东方七宿,角(木蛟)、亢(金龙)、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北方七宿,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㺄)。西方七宿,奎(木狼)、娄(金狗)、胃(土雉)、昴(日鸡)、毕(月乌)、觜(火猴)、参(水猿)。新法更调参水猿于前,觜火猴于后。古法火水之次序,四方颠倒其一方矣。
七谬删除紫气之新
古无四余,汤若望亦云四余自隋唐始有。四余者,紫气,月孛(bèi),罗喉,计都也。如真见其为无,则四余应当尽削;若以隋唐宋历之为有,则四余应当尽存。何故存罗计、月孛,而独删一紫气?苟以紫气为无体,则罗计、月孛曷尝有体耶?若望之言曰,月孛是一片白气,在月之上。如果有白气在月上,则月孛一日同月行十三度,二日四时过一宫,何故九月始过一宫耶?况月上之白气有谁见耶?
八谬颠倒罗计之新
罗计自隋唐始有,若望亦遵用罗计,是袭古法而不可言新法也。其所谓新者,不过以罗为计,以计为罗尔。但不知若望何以知隋唐之罗是计,计是罗耶?罗属火,计属土,火土异用,生克制化,各有不同。敬授人时,以前民用,颠倒五行,令民何所适从!
九谬黄道算节气之新
按:节气当从赤道十二宫匀分,每一节气该一十五日二时五刻一十七秒七十微八十三。今新法以黄道阔狭之宫算节气,故有十六日、十五日、十四日一节气之差,所以四立二分皆错日,二至错时。
十谬 历止二百年之新
臣子于君必以万寿为祝,愿国祚之无疆。孟子云“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言千万年之历可前知也。太宗皇帝仁武而不嗜杀,天故笃生;皇上冲龄,而为一代开辟之主;皇上又英明仁武而不好杀,天将笃祜。皇家享无疆之历祚,而若望进二百年之历,其罪曷可胜诛!
顺治十六(1642年) 年五月 日
原论繁冗,反不达意,部审入招,节略如右,以便翻清入疏进呈。
附始信录序(一)
宇宙间奇峰峭壁,必有峡崥(pí)为之基,以成其峻拔之势,未有无所凭藉,而能成其为崔巍者。惟新安黄山之始信峰,如攒万片竹木,不著一寸土壤,拔地而起,矗立千仞,四面陡绝,莫可跻攀。欲登者,由如来峰编木为梁,广不盈尺,修不逾丈,架为飞虹。有松焉,名曰“接引”,横出一枝,正与腰平,直达彼岸。人扶以渡峰顶,大可函丈,一废团瓢,才能容膝,以憩游人。四面群峰如架上槊(shuò),如筒中笔,林立天外。登者莫不跳跃叫绝,以为不登此巅,不信人间有此奇峰,故以“始信”名焉。
吾郡杨长公先生,身不列于宫墙,名不挂于仕版,虽有令先大宗伯世荫,又逊职以为布衣。论其时地,不过一齐民尔。一旦起而劾权要,其先后章疏与《正阳忠告》诸刻(二),顿令长安纸贵。当其舁(yú)棺之日,赠诗者盈棺;廷杖之日,观者万人,靡不为先生称佛名号。而先生之奇,始信于天下。癸未冬,烈皇御经筵,询宇内文武材,廷臣以闽抚朱之冯对(三),襄城伯李国桢以先生对(四)。帝曰:“是舁(yú)榇(chèn)之杨光先乎?”遂悬大将军印,以待先生。襄城遣人迎,未至先生所,而宗社墟矣。编《明纪》者,数家咸书先生劾温首(五)、揆(kuǐ)者陈吏垣(六),获谴杖戌事,而先生之奇始信于后世。然予以为犹未足尽先生之真奇也。先生之真奇,不在于劾权要,而在于尊圣学,缅维止至善之道。惟学力以致之,非学脉则道脉不明。先生疏中,生民以来,圣圣相承,惟此道统历千世而不坠。赖有圣学之《六百三十四言》(七),其有功于学脉道脉至矣,尽矣!诚古今来不再见之鸿文,真足与天地并垂不朽。较汉、宋诸儒之羽翼圣经者,功高倍蓰(xǐ),而编年家不知收此,而收劾权要之事,可谓拾其细而遗其大矣。《资治纲目·凡例》,凡关道术者必书,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可云不关道术乎哉!可以不大书特书乎哉?予未免有史才而无史识之叹。后有正史必以予言为归。从来理学经济名臣垂于竹帛者,率在身后;而先生以无位之布衣,标青史于生前,岂非古今之至奇者哉?不读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不信人间有杨先生;读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始信人间有杨先生也。先生一生,精神事业专致力于宫墙。近著《辟邪论》《中星说》与《六百三十四言》相为表里,合而观之,功不在孟子下矣。峰之始信,人之始信,咸于吾郡见之。地灵人杰,信矣哉!兹合先生之四文,题曰“始信”,另梓成帙(八),以与天下后世共瞻先生之真奇。
顺治庚子(1660年) 仲冬吉旦眷娃王泰征顿首拜书于紫阳之讲席。
邪教以序内有“明史”二字,首告光先到部,冀脱彼罪。蒙部审取光先口供,犹记其大略,谨录于左。朝廷诛庄逆之《明史》,诛其言语不伦,非诛“明史”二字。从来墟社之史,新朝修之,考其一代政令之得失,善者取以为法于后世,不善者取以垂戒于后世,此历代修史之意。如周秦史汉修,汉史魏修,魏史晋修,晋史隋修,隋史唐修,唐史宋修,宋史元修,元史明修,明史应该清朝命文武大臣总裁开局,令词臣纂修。因明朝天启、崇祯未有《实录》,加以朝报散失,无凭稽考,故未举行。所以田间留心古今政事之士,著有《明纪史略》,谓之野史。朝廷开局纂修之史,谓之正史,野史适以备正史之采择。无野史则正史无所考衷,正史出而野史自然不存。“明史”二字不在叛逆之科。
(一)“始信录序”及以下一篇“尊圣学疏”前“附”字原无,今据前《目录》加。
(二)《正阳忠告》疑佚,内容为讥陈启新之作。见《四叩阍辞疏》。
(三)朱之冯:明末殉节名臣,《明史》有传。
(四)李国桢:明初都指挥使、襄城伯李睿后裔,《明史》传附李睿。
(五)温首,即温体仁,《明史》有传。
(六)陈吏垣,即陈启新。《明史》有传附姜埰。
(七)《六百三十四言》:疑即下篇《尊圣学疏》,全文约六百余字,故名。
(八)《始信录》今不见流传,疑佚。又,“四文”,上只提到三篇,另一篇为何,不详。
附尊圣学疏
恩荫新安卫官生、今让职杨光先,为臣疏裕国恤民等事。内云吏科给事中陈启新假尊经,以纠马之骊之不尊经(一),而追论宋室变华为夷皆学之罪;坏万世人心道术由宋真宗劝学之歌(二)。如此作孽,真不容于天地间矣。生民以来圣圣相承,惟此道统历千世而不坠,赖有圣学圣经一章,冠以《大学》之道。《论语》一书,首言“学而时习”。从来大圣大贤,孰非学力所致?学之在天地间,如日月之无终无古,有明晦而无消歇。世隆则从而隆,世污则从而污。求真黜伪,古道綦(qí)严,未闻学可罪也。即否塞如元末之世,天地亦几息矣,而刘基、宋濂、陈遇、陶安、王祎、章溢之徒(三),不以时之左文而贬其学。洎(jì)高皇帝崛起滁阳,辟既昏之天地而大明之,诸儒应运云从,遂为昭代儒宗之首。继而方孝孺、黄观、铁铉、景清辈(四),又为万世忠孝之冠。后此则钱唐之袒胸受箭(五),李时勉之肋折金瓜(?爪)(六),于谦之旋乾转坤,王守仁之武功文德,杨继盛之批鳞触奸,海瑞之刚直廉介,吴与弼、陈继儒之道学文章(七),洁身高尚,是皆未绝之读书种子。而伦常之事,赖以扶植。其他理学、经济、忠节、清贞,不可胜数,而启新至谓太祖竭尽心力,未见大有挽回。何其敢于诬先圣,诬祖宗,诬名臣之若是!皇上敬天法祖,尊经黜异,直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脉,帝王之学,唯皇上独得其宗。臣惟恐皇上学之不笃,好之不专,使伪君子、假道学布列朝宗,令谠言日辣,惠政日壅,致天下日趋于乱,是为深忧。今启新以一时之鲜实行,而径归罪于宋宗之歌《劝学》,是欲皇上废先圣之学矣。以尊经为名而以废学为实,古今有此尊经之体否?臣谓折棚破榜之妖风,(丙子科榜出之日,妖风碎榜,吹倒榜棚。)正应启新厌学之一疏。此上天先圣所以提醒首善一榜之人以转告夫天下学者。启新本意,不过欲申前罢制科之论,故作此巧语以动皇上。臣观启新之意,未止于罢制科;启新苟得大用,不至于焚书坑儒不已。噫,尧舜之世不容四凶,而圣明在上,岂可储一妖祟之李斯乎?此天地间无等之罪人,臣不知皇上何以待之也。
(一)马之骊:生平事迹无考。
(二)劝学歌,亦作《劝学文》。全文曰:“富贵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随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三)陈遇、陶安、王祎、章溢,皆明初儒臣,事迹均见《明史》本传。
(四)方孝孺、黄观、铁铉、景清,皆“靖难”节烈名臣,事迹均见《明史》本传。
(五)钱唐,原作“钱塘”,误。洪武年间出任刑部尚书。时太祖阅《孟子》,读至“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句,谓非臣子所宜言。乃欲罢其配享,有谏者,咸命金吾射之。钱唐不顾,仍上言愿为孟子袒胸受箭,帝始悟。《明史》卷一三九有传。
(六)李时勉:名懋,以字行,江西安福人,永乐二年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兼经筵官。《明史》有传。“肋折金爪”,指其于仁宗时,因上言忤旨,被武士以金爪打断三根肋骨事。
(七)吴与弼、陈继儒,均明代理学家,事迹见《明史》本传。
本文由汉语基督教研究网[ChineseCS.cc]—汉语基督教文献馆[CCT.ChineseCS.cc]发布。该文章由本站收集、整理、录入!请勿他用,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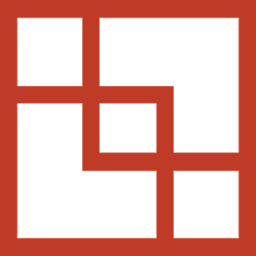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