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个世纪前中国就建立了犹太人的会堂,这一消息对于所有欧洲饱学之士来说是最让人感兴趣的消息之一。他们暗自庆幸,这一下他们可以找到一部《圣经》正本,可用于解释清楚他们的难点,结束他们的争论。然而,有幸做此发现的利玛窦神父没有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有利结果。由于传教任务的需要,他没法离开北京,不能亲自到远离北京近200法里的河南省省府开封去。 他只能询问一名他在北京遇到的该会堂的年轻犹太人。他由此知在开封府居住着10至12户家庭的犹太人。他们刚刚在那里建女了他们的会堂,自从五六百年来,他们非常恭敬地保留着一部非常古老的《摩西五经》。利玛窦神父马上给他看了一部希伯来文的圣经。那位年轻的犹太人认出那字,但不会阅读,因为自他们认字始,他们读的都是汉语书。 利玛窦神父紧张的工作没能使他将发现再推进一步。只是三四年后,他才有机会派出一名中国的耶稣会士前往开封,去证实他从主轻犹太人那里所听说的情况。他让中国耶稣会士带上他给会堂掌管的一封中文信。他指出,除了《旧约》以外,他还有所有的《新约》,表明他们等待的弥赛亚(救世主)已经来了。那会堂掌教读到关于弥赛亚降临的段落,就停下来说,这事还没发生,因为一万年,他们才能等到。但他托耶稣会士向利玛窦神父请求(他知道利玛窦神父博学多能的名声),请他到开封来,他非常高兴将会堂交给他管理,只要他不吃犹太人禁食的猪肉。掌教年事已高,而他也不知道他的接班人是谁,因此决定托付给利玛窦神父。当时的情形非常适于了解他们的《摩西五经》。掌教非常愿意拿出所有章节开篇和结尾。它们被发现与巴勒斯坦的希伯来文圣经完全一样,只是在中国的版本中没有标出元音记号。 1613年,以博学和聪明被中国人称为“欧洲孔夫子”的艾儒略神父得到上司命令前往开封府,作进一步探查。他是世界上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他精通希伯来文。但时过境迁,老掌教已死。 他们让艾儒略神父看了会堂,但艾儒略神父却始终无法让他们给他看那些书,甚至连遮盖这些书的帐幕都不愿拉开。 以上就是这项发现初步的开端,这一切都是由金尼阁神父和曾德昭神父及其他传教士向我们转述的。博学之士也常常谈起,有时常常不太确切,却总是希望知道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随后,耶稣会士在开封建立了住所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安国宁(又名李西满)神父和费乐德神父想利用他们的有利条件,但劳而无功。第一个取得成功的是骆保禄神父。他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会堂,拓下一片会堂的碑文(刻在巨大的大理石片上),并送到了罗马。这些犹太人告诉他,在北京的藏经阁里有一部圣经。法国和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得到皇帝的准许,进入了藏经阁,看了那里的书。巴多明神父当时在场。但人们没有什么发现。白晋神父说,人们只看到一些古叙利亚语的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藏经阁的主人没有给耶稣会士们充分的了解。今天要再进入藏经阁已经非常困难,宋君荣神父千方百计想进入都未能奏效。他永远无法知道这些希伯来文和古叙利亚文的书究竟是些什么书。但是,一位满族基督教徒(宋君荣曾将一本希伯来文的圣经借给他)对宋君荣说,他曾经看到过一些书,上面的字与这本圣经上的字一样,但他说不出这是些什么书,也说不出这些书的年代。他只是向他肯定其中有一部《托拉》,即犹太教的经书。 当北京的耶稣会士调查没有进展的时候,比中国人要较少神秘性的犹太人非常愿意向骆保禄神父介绍他们不同的习俗,于是骆保禄神父才能写出我们从一位不懂希伯来文的人身上所能期望的最详尽的报告。该报告发表现收录在本书第十卷(第17页)(参见本书中译本第二卷第11页)。 这些新的知识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艾田·苏西埃神父当时正考虑写一部关于《圣经》的重要著作,他以最大的热情来推动这一发现。我在本报告中所叙述的一切都来自骆保禄神父、孟正气神父和宋君荣神父给苏西埃神父关于这一问题的信件。由于人们期待已久,杜赫德神父在《中华帝国全志》中也欣然作了承诺,因此关于此问题的详细情况弥足珍贵。 中国人称与他们共处的犹太人为“回回”,与伊斯兰教徒相同。但犹太人自称“挑筋教”,即“那些将筋割断的人的宗教”,因为他们的宗教为了纪念雅各与天使的战斗,禁吃大腿筋。他们在会堂祈祷时戴蓝色小帽,因此人们也称他们为“蓝帽回回”,以区别于穆斯林,因为穆斯林戴白色小 帽,他们被称为“白帽回”。 这些犹太人说,他们在汉代明帝统治时期进入中国,他们来自“西域”,也即西方的国度。根据能从他们嘴里的所有东西,这个西方的国度似乎是波斯,他们经呼罗珊和撒马尔罕来到中国。他们的语言中还保留着一些波斯词语,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与该国保持广泛的联系。他们认为他们是在这块广袤的大陆上惟一立足的犹太人,他们和在印度、西藏、西方鞑靼之地的其他犹太人互不相识。长期以来,他们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他们中出过几个省的长官、国家大臣、秀才和举人等等,也有人拥有巨大的地产。但时至今日,他们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他们在杭州、宁波、北京和宁夏的居住地消失了。大部分人改信了伊斯兰教。现在人们所知的只剩开封府的一支。他们总计七十多家,在他们来定居的时候,分成了不同的部落,如便雅悯部、利未部、犹大部等。现在他们减为七个家族,总共至多千人。该城市最近一个时期遭受到的各种灾难造成了他们的衰败。 在万历年间,一场大火将他们的会堂化为灰烬。所有的书都化为乌有,只剩下一部《摩西五经》。此书是在此前一次更悲惨的事件后,他们从一位在宁夏遇到的穆斯林手中得到的。一位广东的犹太人在临死之前将此书作为非常珍贵的收藏交给了那位穆斯林。他们重建了会堂,但在1642年的黄河大水中又遭毁坏,这场水灾造成三十多万人丧生。 犹太籍的政府官员赵负责会堂的重建,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会堂。他们称之为“礼拜寺”,其意为“举行仪式的地方”。这幢建筑仅60法尺长,40法尺宽。但加上它的附属建筑,占地150法尺宽,300—400法尺长。孟正气神父曾绘有这些建筑的平面图。 会堂的大门面东。大门后面有一座“牌楼”,即有一座凯旋门直通大院,在大院的出口处又是一座新的凯旋门,在两边人们看到有两块石碑,上面的碑文我将在报告的最后会再提及。再往前走,我们可以看到两头放置在石墩上的大理石狮子,两只焚香用的香炉,两只有底座的铜盆和两只大花瓶。最后人们到达礼拜寺前的广场,它的周围均围以栏杆,正是此处,人们搭帐篷以度住棚节。 礼拜寺两侧低平,大殿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放着摩西讲道台、“万岁牌”即皇帝的牌位和一张放置香烛的大桌子。在皇帝的牌位的桌子上,人们看到用金字烫成的希伯来文碑文:以色列人啊,你要听,吾神耶和华是惟一的神。感恩吾主名,祂的统治光耀千秋。 第二部分由一顶外方内圆的帐篷组成,这是中国犹太人的圣人至圣之所。他们称之为“Bethel”,汉语叫做“天堂”,即“天上的寺庙”之意。在帐篷的正面,人们读到烫金的希伯来文的碑文:“应知耶和华是众神之神,是吾主,是伟大、强大、恐怖之神。”这个深受中国犹太人崇敬的地方放着他们的“大经”,即他们与《圣经》有关的圣书。在Bethel的边上,有一批壁橱,“大经”和其他用书就放在里面。在Bethel的后边,是两张桌子,上面有用金字写成的教义。 在所有这些文物中,欧洲学者最感兴趣的就是“大经”。但为了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中国犹太人所说的“大经”仅指《摩西五经》。在他们的Bethel里,一共有十三部抄本,分别放在十三张桌子上,以纪念十二个部落和宗教的创始人摩西。这些经书不是如骆保禄神父所说是写在羊皮纸上的,而是写在普通纸上的,人们将几张纸叠粘在一起,使纸卷起来不易破碎。 每部Bethel里的大经都卷在一根轴上,形状像一顶帐篷,上覆丝幕。犹太人对所有这些书都最为崇敬,而所有书中又有一部是他们最最崇敬的。据他们说,此书已有三千年的历史了,这是他们惟一留存的文物。其他的书都在火灾和水灾中被毁,现在这些书都是根据波斯人的书复原的。 所有Bethel里的大经都是没有标点的。它们被分成五十三段。人们在每个安息日念一段。因此,中国的犹太人和欧洲的犹太人一样,念完他们的经文要一年的时间。读经者将大经放在摩西的讲道台上,他的脸上蒙一块极细薄的棉纱。他边上有一位提台词者,在他下面几步还有一位“莫拉”,如果提台词人讲错了,他再负责纠正。孟正气神父在这“礼拜寺”里没有看到手提香炉,没看到有什么乐器,没看到为举行仪式而穿着的盛装。一切简化到不穿拖鞋就行,所有的人头上戴一顶蓝色小帽。只有在住棚节,人们才能看到大经的游行队伍,持大经者从右肩到左臂下斜挎一条红色塔夫绸巾。 在孟正气神父在开封的八个月里,他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要得到 一部大经,或至少能允许他拿一部抄本与他的圣经作点核对,但都无济于事。他不能说服那些由于无知而对一切都心存疑虑的人。他们给他的惟一优惠是让他看一眼他们的书,允许他查阅某些段落。下面就是孟正气神父告诉我们的一些情况。Bethel里的大经是用圆字写成,没有标点。字体接近于德意志的希伯来文版本。人们既看不到Phcthura,也看不到Sethuma。所有的都连在一起,只是五十三段的每一段留有一行空间。人们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的抄本上没有标点时,他们回答说,天主口述摩西律法时,速度太快了,根本没有时间去标点。但他们西方的博士们根据他们的理解加上了标点,便于阅读。 在住棚节最后一天的礼拜六,孟正气神父前往会堂,他们给他看了他们最古老的大经。它有2法尺高,卷起来时,它的直径还略长一点。它看上去非常古老,而且已受到严重的水毁。孟正气神父问今天念到哪一课。他们指给他看摩西的圣歌,在犹太人那里,这就是第五十二段Va jelec的一部分。他们的五十三段与我们圣经的五十四段相同。他们高声朗读起摩西的圣歌。它被写成两列,与我们的圣经完全相同,但有的行有点重叠,看上去模糊不清。在这首圣歌中,孟神父发现惟一不同的地方是在第二十五行,我们圣经中“thesca一ce1”一词在大经中成了“thocel”。((申命记)第32章,第25行)这一差异并不改变原来的意思:摧毁人和吞噬人的刀剑始终会为天主对以色列人的亵渎进行复仇。 放在壁橱里的大经都有元音符号,字体非常像1705年在阿姆斯特丹刊印的阿提亚圣经上的字,但大经上的字更漂亮、更大、更黑。所有的字都用像我们鹅毛笔那样头尖的竹制毛笔手工抄写,墨水是他们自制的好墨水,每年在住棚节时都要换新的墨水,因为他们在用中国笔和墨水时非常仔细谨慎。但他们在使用中国纸方面就没有那样精细。他们没有用明矾水处理,以便两边都能书写,他们更喜欢将几张纸叠粘在一起,做成一张比平常纸厚三四倍的纸。 这些大经约7法寸宽,4—5法寸高,由五十三册组成。每册书包括《摩西五经》的一段,第一段的第一个词不用起首大写字母,也不标音符,写在第一页白边中间一块绿色或蓝色的长方形的小丝绸片上,或写在白色的塔夫绸上。如第一册写着:Bereschith(起初),第二册写着:Noach(诺亚),其余各册大体如此。段落划分与阿姆斯特丹圣经相同,除了第五十二段和第五十三段,他们并为一段。写在第一页页边的第一个词并不重复出现,每一页用数词来表示,而不是用数字字母来表示,这一数词总是在书中第一个词的上方。 由于每一段独立分册,所以在段的末尾,就不必标注Phethura符号和Sethuma符号。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这些分割符一无所知,尽管这些分割符在他们的书中比我们的书中要少见得多。他们有时也用在页边,始终有两种方式。在Bereschith这一册(《创世记》的第一 段)里出现四处:第一处出现在第一章第十行前(根据我们的计数), 第二处出现在同一章第二十七行前,第三处出现在第二章第二十一行前,第四处出现在第三章第十四行前。除去这四处,整个《创世记》第一段不再有任何的边注、空白和行间分割。他们丝毫不知道使用 Keri符号和Ketib符号。他们在句子末尾标上Pesukim符号,即两点,他们称之为“kela”。至于句子的数目,他们只在一段的末尾或一册的末尾标明,一般标在最后一行的下方,用数字字母表示。“起始”册,即第一册,他们计一百四十六句,第二册“诺亚”册计一百四十三句。 他们有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Bereschith有一个大写的beth字母,在《创世记》第二章第四句中的Behibaram一词中有一个小写的he字母。孟正气神父不相信这些犹太人能够懂得,这些词能分成两种意思,或两种意思能组成一个词,或者这些词取代了其他的词,或者有些词没写出来但它表示出来了,有些词写在那边却并不表示任何意思等等。但是,他没敢这样说出来,因为他没有时间在这一点上再作充分详细的了解。 至于难以表达的天主的名字耶和华(JEHOVA),他们叫成Hotoi。Adonai,他们改叫成Etunoi。在Elohim这个词的发音上,他们没有什么两样。但当他们将耶和华译成中文名时,他们不像传教士那样称为“天主”,而简单地称为“天”,就像中国的文人在解释他们“天主”这一词的意思时所说的那样。 孟正气神父注意到的大经与阿姆斯特丹圣经最突出的不同在于raphe,即横线,这些犹太人称之为lofi。在他们的文本里,这一横线非常普遍,经常一个词有二三个字母上有这一标记。因此,他们的重音在位置和方式上都略有不同。据孟正气神父推测,他们的圣经可能是雅各·本·拿弗他利的东方圣经,在本·阿舍在巴勒斯坦举办神学院时,拿弗他利在巴比伦开办了他的神学院。但这些犹太人对这位犹太教法学博士却一无所知。他们关于标点的知识非常有限。他们不知道我们在欧洲书里看到的那一整套名称。他们泛泛地用siman这个词来表示标点和重音。 现在让我们回到孟正气神父所做的阿姆斯特丹圣经与中国古老大经的对比上来。他们曾要求孟正气神父确认一下《创世记》中几个争论最多的地方。他看了一下,没发现有什么不同。在第23章的第2句中,他没有看到libechotha一词中的chaph字母明显缩小。但会堂的掌教说以前是这样的。对第24章第2句,他们似乎并不用这样古老的方式宣誓。他们之中没有这样的习俗。他们只是不到有偶像的庙里去宣誓。在第33章第4句vajiscake一词中有六个点,第一个点似乎比句号还要大。 他们大经的第12段与阿姆斯特丹圣经一样也开始于第47章第28句的vejchi一词。这一段包括了所有雅各对他的儿子们所作的预言。它们被连续写下来,中间没有分割,也没有phethura符号和sethuma符号。 孟正气神父问他们,他们是如何理解在圣经中经常出现siloh一词和jescuatheca一词,但他们一点都回答不上来。这些犹太人现在已经不能完全理解他们整个文本了。 他们还请孟正气神父看第47章第30句hammitta一词,问他该如何标读,想知道他们应该写成hammitta还是hammatte。孟正气神父忘了;但他认为,在其他地方已经发现与阿姆斯特丹圣经如多的一致之处后,最有可能的是阿姆斯特丹圣经在这一词上也是同样的。 现在,关于孟正气神父的发现还剩两项要提到的。在Beres— chith,即大经第一册书的末尾,他发现了一段碑文,他寄过来的复本已经严重变形,但人们可以认出其中不同的犹太教法学博士的名字。 它似乎是一份对这些博士表示感谢的证据,特别是感谢一位来自麦地那的博士,可能正是这位博士给了他们这部大经。碑文最后写道:“祝福你,这位来者;祝福你,这位归者。拥有了财富,莫大荣耀。主啊,我等待您的拯救。” 孟正气神父还看到张贴在“礼拜寺”柱子上的一张图表,上面标明了诵读《摩西五经》的顺序,他们称之为mineaha。图表上标有两端,分别提到两本我所不知的书。一本叫做Noumaha,它分为十二部分,人们念它是在每个大月的第一天、小月的第二天。另一本叫做 Mouphtar,同样也分成十二部分,人们读它是在大月的十五、小月的十六。孟正气神父想知道这两本书的内容,但这些犹太人的特殊发音使他难以理解他们所说的。 至此,人们也许会认为中国的犹太人除了《摩西五经》外,没有其他的圣经的书了。但这是错的:他们还有其他的圣书,但他们认为的正经只有《摩西五经》。其他的书,他们叫做“圣书”,即补充之书,或分开的书。在这类书中包括了不太完整的《约书亚记》和《士师记》,包括了完整的《撒母耳记》,包括了有些地方被损毁的《列王纪》的最后两书,包括了没有考察它完整性的《诗篇》。 第一部分的圣书共有三十多卷。第二部分包含了hafoutala。他们就是这样来称呼haphtaroth的,即《先知书》的各段落。他们说,以前他们有八十多卷。我们可以相信这一说,因为他们的书所包含的章节不太多,而且在《先知书》中还加入了《历代志》的内容。《以赛亚书》,他们称之为Isehaha;《耶利米书》,他们称之为Jameleiohum。这两书几乎是完整的。他们在节日里朗读它们。他们没有《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他们只有第一章的寥寥几行。 至于那些小先知书,他们只有《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和《撒加利亚书》。这些书大半不全。他们没有其他的小先知书。 《历代志》(他们称之为JP:iveli—Haiamiim)也残缺不全,他们只保留前面4—5章。《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损毁得少一些。中国的犹太人对以斯帖这位王后怀有最高的尊敬。他们总是叫她以斯帖妈妈。他们的尊敬还延伸到末底改身上,他们称之Molitoghi。他们把他俩看做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他们书中在欧洲最为人重视的是《马加比传》的前面两本书。他们似乎称之为Mantiiohum。他们也只有孤本。孟正气神父想尽一切办法想买下它,或至少能得到抄本。但他们连这样的建议都不想听。 在这些“圣书”之外,这些犹太人还有他们的“礼拜书”,即他们的祈祷用书。每部“礼拜书”含有五十至五十二册。它们都用大字写成。书卷就像欧洲和中国的书一样,书高超过书宽,有一指厚。这些祈祷词几乎全部来自圣经,尤其是《诗篇》。最后,他们还有四本Mischna的书和各种不太有序的解释,他们用汉语称为“tiang-tchang”。 他们尽管有这么多书,孟正气神父却发现这些犹太人非常无知。 最机灵的人也只能领会《创世记》和其他他们经常诵读书的若干个地方。对于此弱点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归因于一个多世纪以来,再也没有西域(即西方)的博士到他们这里来过,他们已经丢失了他们的《读经本》,即他们的语法书或有助于了解圣经的书。 骆保禄神父补充说,当他们抽签的时候,要用他们的宗教书籍。在出生的第七天,他们要行割礼。在安息13,他们家中不生火。除了安息日,他们还有逾越节和其他的一些庄重的节日。有一天,他们全体会到犹太会堂里痛哭呻吟。他们知道大天使、小天使和六翼天使。骆保禄神父曾经向他们提及有关弥赛亚的问题,却从来得不到任何答案。他们从来不接受新人教者,从来不和外国人通婚。他们只用汉语印刷极小的宗教书,当遭遇迫害时,他们向官员上交的就是这种书。 他们的文人和饱学之士尊崇孔夫子。他们也尊崇所有已去世的祖先,为其立有中国式的牌位。在他们会堂的墙院里,他们建有一厅,保存他们已故有功者的牌位。在会堂的人口处,有一旧牌坊,上书“敬天”。其字体与康熙皇帝亲笔为耶稣会传教士教堂所提的字相同。 他们祈祷时,面向西方。其会堂也是东西向的。他们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耶路撒冷就在西方。有钱人可以不必去会堂,他们只要请人抄写一部大经,将它放人壁橱之中就足够了。因此,在普通的节日,在礼拜寺,人们只看到四五十人。放在壁橱中的大经是不能拿出会堂的。一位犹太人曾同意将他的大 经卖给孟正气神父。但当孟正气神父将此经带走时,却令他大吃一惊。人们把此书夺了下来,并对他破口大骂。 以上就是当宋君荣神父造访开封时我们对于中国犹太人的一些认识。宋君荣神父在欧洲以他的热忱著称,大家都愿意将一切使他感兴趣的有关亚洲的知识转达给他。他在开封受到很好的接待。他利用这一时机得到了一些新发现,多亏了他我们得到了会堂里的中国碑文。第一块碑立于1444年,(原文如此,可能有误。实际上第一块碑应立于1489年(明弘治二年),下文我们还看到,它提到1462年的大水。一一中译注)人所写。下面是宋君荣神父寄过来的那篇碑文的大概: 一赐乐业(当时对以色列的汉字译写)教创教者为“阿无罗汉”(即亚伯拉罕)。这位圣人生于周朝开始后一百四十六年。他的律法代代相传,传至摩西。他在西奈山接受了律法书。他总是和天主结合在一起。他的书共有五十三段。其中的教义类似中国的五经。作者在此将中国的学说与犹太人的学说相提并论。 他用好几段文字特别论证他们对天的祭拜、他们的仪礼、他们的斋戒、他们的祈祷、他们尊崇死者的方式几乎都和中国一样。他提到在《易经》中人们可以找到安息曰守瞻礼的痕迹。他补充说, 摩西生活在周朝开始后的六百一十三年。他还提到了盖思拉(即以斯拉)。他用自己的热情修复了书籍,教育以色列人,纠正了他们的错误。 在这块碑文上,他们还提到1462年大水摧毁这座会堂的细节,指出宁波和宁夏的犹太人送来书籍以弥补他们的损失。 四川省的大官和财政官Tso—Tang在1515年,即武宗皇帝正德十年,刻了第二块碑。 该碑以这几个字开头:一赐乐业教。阿耽(即亚当)是第一个人。他生于西域之天竺。犹太人有教有传统。教义包含在五部书里,分五十三段。这位中国官员对犹太教大加赞扬,接着他补充道:犹太人像我们一样敬天。亚伯拉罕是他们教义的创立者,是他们的祖先。摩西颁布教义,是他们的立法者。自汉代起,犹太人开始在中国定居。在第六十五个循环的第二十年,他们向孝宗皇帝进贡了印度的丝绸。皇帝愉快地接受了,并同意让他们居住在当时称为汴梁)的开封。于是他们形成了七十个姓(即家族),建造了他们的会堂,将他们的经书,即他们的圣书,放入会堂。 这位官员说,这些经书并不仅仅是为开封的犹太人所写的,它们和所有的人有关,不论是王公还是平民,不论是父亲还是孩子,不论是老人还是青年,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学到他们应尽的义务。作了这 些评价后,这位官员指出,犹太的律法几乎与中国的相同,它们两者的基本点都是敬天、尊祖,给故人以应得的荣誉。这位官员还高度赞扬犹太人。他确认,无论务农经商、做官、从军,他们因其灵巧、忠诚、对礼仪的恪守而得到普遍的尊敬。他最后说,犹太教经亚当传之女娲(即诺亚),诺亚传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传之以撒,以撒传之雅各,雅各传之十二部落,再传之摩西、传之艾伦、传之约书亚、传之以斯拉。最后一人是第二位立法者。 康熙皇帝第二年(1662年),一位担任帝国大臣的大官立了第三块碑。他首先提到了亚当、诺亚、亚伯拉罕和摩西。他给予亚伯拉罕很高的赞誉。他说,亚伯拉罕所敬之天,无形象,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和保护者,是永恒不变的。亚伯拉罕的教义保存至今。接着,他将亚伯拉罕和摩西的时代与中国的皇帝作比较。但此处充满着错误。他又写道:摩西在西奈山接受律法,他斋戒了四十天四十夜,他的心一直升到天主那里,他的律法有五十三段,所有都受人崇敬。他歌颂以斯拉,称他为此教的恢复者。他赞扬犹太人。他指出他们的学说与儒教学说的一致性。他以中国五经的权威为基点,证明在中国古代就有守安息曰的习俗。他进一步推断,希伯来文字与古代中国文字有关系。他详细地描写了1462年摧毁开封会堂的那场大水,当时为天顺皇帝(以前称为正统皇帝)第七年。书籍严重遭毁。一位叫做Yn的宁波犹太人带来了一部圣经,人们就此抄写出所有的经书。1490年,弘治)年,人们重建礼拜寺。Yen—Toula出资建造。 这位官员最后列举中国三大不同的教派。他重复说,犹太教在所有的方面和儒教相一致:敬天、孩子孝顺父母、臣民服从君王、在某些时候要祭奠死者等等。 第四块碑亦即最后一块碑,仍然有对亚伯拉罕的赞颂,称他是亚当的第十九世孙。同时也赞颂摩西、以斯拉,赞颂把“天”(天主)作为万物创造者来崇拜的宗教,其中丝毫没有与犹太人看来的伪神相混淆,他们严格地遵守他们的教义。碑文对1642年的大水有详细的描写。会堂被摧毁,大量犹太人死亡,二十六册经书丢失,其余的被抢救下来。从这些残片中,1654年他们整理出一大卷。在碑上人们可以看到整理和誊写者的名字。掌教(即会堂的首领)复读了全卷。碑文确定一切都准确无误。碑文最后对新建的礼拜寺作了全面的描绘,提到它各种正厅、它的偏殿、它的院子和它的大门等。建造工人的名字也刻在上面,同时上面也有皇帝牌位和Bethel (为犹太圣人们所设之“天堂”)出资者的名字。人们还看到在开封幸存的七个家族的姓氏。 宋君荣神父并不满足于得到这些碑文的拓片,他还和这些犹太人建立了友谊。他调查了他们的信仰和习俗。通过访谈,他了解到他们相信炼狱、地狱、最后审判、天堂、死而复生、天使等等。但他们从不声称是特别的信仰。宋君荣神父向他们解释我们普遍理解的耶和华一词的意思。所有的人为他鼓掌,向他保证,他们历来把这词看做是永恒的天主,它意味着“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和永远存在”。 宋君荣神父认为听一下他们关于细罗一词解释的时机已到,这词在雅各的预言里是如此著名(细罗,意为赐平安者。雅各在临死前对他儿子犹大说:“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顺。”(《圣经.创世记》,第49章第10句)一一中译注)。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个有关于这一词的故事,因此他特别想知道犹太人是怎样理解这一词 的。故事发生在他还在汉口的时候,这是湖广省的重要港口城市,当时Couteux神父正居住在那里。宋君荣神父得悉在Couteux神父家中有位非常博学的中国人,他能够解读非常古老的文字。宋君荣确信“silon”一词是古代某种圣书体,他就请求这位一点也不懂希伯来文的中国学者谈谈他对“silon”一词的感觉。这位中国人将silon字母拆开,按中国书写的方法从上到下写下来。那位中国人一看到这些字母,他就说,第一个意思是“非常高”;第二个字母意思为“主”;第三个是“一个”的意思;第四个是“人”。他补充道,在中国,他们会将这一名字与“圣人”(用法语来说即神圣之人)联系起来。和宋君荣神父一起在场的Couteux神父和雅嘉禄神父都惊讶万分。犹太人的解释也同样令人惊奇。当宋君荣神父问他们这一问题时,开始全场鸦雀无声。他开始解释神父们和神学博士们对这一词的理解。这时,一位年轻的犹太人非常有礼貌地请求讲话,他说,自己一位已经死去多年的叔公向他证实过,该词中有些神圣的意思,第一个字母意思为“伟大”,第二个字母“一个”的意思,第三个字母的意思是“从天而降”,第四个字母是“人”。这是天主救世主非常特别的表示方法,表示他从天上降到地上。那位年轻的犹太人又说,除此之外他就不知道其他什么了。这位年轻人引起了宋君荣神父的爱怜,宋神父跟上他,问,姓甚名谁,家住何处,答应他会经常关心他的消息。 在离开会堂之前,宋君荣神父要求看一下他们的书。掌教同意了。除了我上面已经提及的书之外,他们还给他看了一部迄今为止一直瞒着传教士的书。由于该书非常特殊,它使得宋君荣神父全神贯注。这是《摩西五经》的残本,似乎受到水的严重浸损。它写在非常好的纸卷上,字体大而清晰,有点类似安特卫普圣经本上的希伯宋体,又类似1531年维登堡印刷的希伯来文和迦勒底文语法书上的希伯来体,介于两者之间。字母下面没有标识,而在字母上面有重读符号和据宋君荣神父说他从未见过的一些标识。他向掌教询问了有关这部看上去十分古老的手稿的情况,下面就是他了解到的情况。在万历皇帝年间,会堂被烧毁,所有的书再次被毁。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域的犹太人到达这里,他们从这些人手里得到了圣经和其他一些书。这部《摩西五经》是他们惟一保存下来的原本,其他的书,他们只有抄本,而这些抄本也随时间流逝而丢失了。宋君荣神父想出巨资得到这部《摩西五经》,被拒绝了。但他们答应以合适的价格给他一部复本。 然后,他要求在场的犹太人对书中一些地方作一些解释。这些犹太人以各种理由推托,他们说,西方的大师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了,他们丢失了他们的“读经本”,除了《摩西五经》他们还能领会一二外,他们不能解释其他圣经的书,读不懂这些书的解释,也不能读懂他们残存的“密西拿”(在希伯来文中原意为“重新阐述”,它是犹太教口传律法总集。一一中译注)。 接着轮到他们要求宋君荣神父为他们解释一些事情。宋君荣神父讲解了雅各的预言、天主的十诫、只承认一个神的箴言。他还想向他们解释从以撒至摩西来临的段落,但在他们给他的书里这一部分被撕破了。他只好向他们讲解这一段的故事,他们似乎对宋君荣神父所讲非常满意。 接着,一位犹太人拿着书,解释这一句:“以色列啊,你要听,你的主人你的神是惟一的神。”他也解释了行割礼的箴言.但这些犹太人的发音非常独特,所以当这些犹太人不看着书本念希伯来文时,宋君荣神父只有猜测的份了。 不难设想,这些犹太人很久以来已经失去了与西方犹太人的贸易往来,他们生于中国,他们不能听到我们的一些声音,他们甚至没有了B、D、E、R这些字母,被迫用P来代替B的发音,用T来代替D的发音,用ie宋代替E的发音,用L代替R的发音。还有他们在发一些元音时,带很重的鼻音,尤其是发元音“hu”这个音时。因此我们的“tohu va bohu”,他们发成“theohum VO peohum”。“thora”他们发成“thaulaha”或“thaulatse”;“bereschith”发成“pielechitsce”;“schemoth”发成“schemesse”;“bmidar”发成“piemizpaul”;“debarim”发成“teveli一im”。 宋君荣神父对他所得到的信息非常满足,对受到的友好接待也非常高兴,于是离开开封,动身回到北京,希望不久能得到他所看到的那本独特的《摩西五经》的复本,已经计划第二次去开封,完成他刚刚顺利开始的调查。然而,接着而来的宗教变故摧毁了我们在开封的住所,中断了我们已经建立的与犹太人的联络。 在我将分散在传教士们书信手稿中我能找到的东西细心地集合在一起后,留下我还能做的只有在某些我认为值得讨论的方面提出一些思考意见。这些我留待在报告末尾,是为了保证叙述他们详细发现的连续性,我的思想和我的推断不能代替他们直接的观察。 根据以上的碑文,亚当出生在“天竺”。中国用“天竺”指称五个不同的国家,两个最著名的国度,一是印度部分,靠近“佛”(Fo)所诞生的孟加拉王国;另一个是包括麦地那的叙利亚,所以碑文上所说的天竺可能指的是叙利亚。在古代的时候,他们称之为“天堂”,即“天之国”。今天他们还称之为“天方” 这些犹太人不知道圣路加和塞帕坦特圣经讲到过的小该南,既然他们说亚伯拉罕是亚当的第十九代孙。 他们将亚伯拉罕的时期等同于周朝的第一百四十六年,这是最难于理解的。中国的这一朝代开始于耶稣纪年(公元)前的1122年,而亚伯拉罕死的时间先于耶稣纪年十八个世纪还多。我在宋君荣神父关于中国编年史的著作中找到了这一难题的解决方法,它完全说得过去。他指出,周朝在中国登天主位之前,曾经是一个小王国,该家族的首领后稷以及其后代在历史上只取得国王的称谓。 但后稷的时代可以上溯到几近尧帝的时代。尧开始统治中国的时间至少为耶稣纪年(公元)前1226年( 原文如此,可能为2126年之误。一一中译注)。这样,亚伯拉罕的时代可以相当于以后稷为首领的周家族的第一百四十六年。 这一方法同样也可以解释摩西的时代问题,在碑文上他们称摩西生于周朝第六百一十三年。剩下的难题是,碑文上所推定的亚伯拉罕的年代和摩西的年代相差四百六十七年,而亚伯拉罕和摩西的出生年代只相差四百二十五年,这样就多出了四十二年。我个人的推断是,这四十二年是摩西住在埃及法老家中的时间,此时他正接受埃及学问的教育。中国的犹太人可能根据某种传统或相似的东西,将这位伟大人物开始焕发热情拯救子民的日子看成他出生的年代。 关于《大经》的古老问题,这些犹太人曾对孟正气神父说过,他们拥有这部书已有三千年。其实非常明显,他们所说的不是一部三千多年的手稿,而指的是三千年前摩西接受的犹太律法。从犹太律法 在西奈山颁布到这些犹太人对孟正气神父说话时为止,根据欧洲犹太人的一般计算正好为三千年,这也证明了中国犹太人的纪年方法和欧洲犹太人是相同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犹太人进人中国的时间。他们对所有的传教一直说,他们是在汉朝统治时期进入中国的,他们的碑文也这样说。 汉朝开始于公元前206年,正是在这个时期,犹太人开始渗透到中国,这似乎是在他们帝国崩溃之前他们就到中国去了。但最符合自然的事情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的大灾难后,犹太人四处逃散,在呼罗珊和特兰索克萨纳地区的犹太人扩散到中国。这一推断甚至与确切的事实非常接近,因为我想到,有些犹太人非常确定地说,犹太人是在汉明帝时到达中国的。这位君主登基的时间是公元56年,死于公元78年。这一时间正好与耶路撒冷被毁相吻合,耶路撒冷被毁发生在公元70年。 ② 古代中亚地区地名,主要城市为撒马尔罕。一一中译注 开封居住点的形成是更为晚近的事。第二块碑告诉了我们年代,即第六十五周期的第二十年,这一年他们向孝宗皇帝进贡了印度织物等。所有这些文字都对应了公元1163年,也即孝宗皇帝统治的第一年。在前一年岁末,高宗皇帝将对国家的统治权转交给孝宗。这是他所能挑选的最积极、最有能力抵御鞑靼军队的君王,也只有这位君王能够扩大中国人在开封东部所刚刚取得的胜利。会堂所遭受的灾难在碑文中都一一注明。1462年,它遭受黄河(即黄色的河流)大水的损坏,这条河以水灾闻名,俯视着开封城。几乎所有的书都丢失了,留下来的也遭到水毁。1642年,该城被反抗正统王朝的中国人所围,但该城竭力抵抗,以至于残酷的李自成被迫两次放弃对该城的包围。第三次他又来围城,并以饥饿威胁他们投降。眼看弹尽粮绝的总督叫人扒开了黄河大堤,迫使敌军撤退,结果自己也被大水所淹。会堂再一次受损,又丢失了一些书。 这两次大水之间,在16世纪末万历年间(万历皇帝于1572年登基),会堂又遭火焚。在这次灾难中,书籍第二次被毁。 尽管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我们仍旧从这些犹太人身上得到了有关他们风俗和书籍的珍贵信息。他们的《摩西五经》与我们的相一致给了我们进行证明的新动力,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摩西书中得到了许多有利于宗教的证明。传教士如能为欧洲得到一部放置在会堂圣所里的《大经》,或至少一本与最古老的手稿准确核对过的书,他们就可以圆满完成他们的任务了。宋君荣神父最后看到的那部《摩西五经》要求我们对此作新的和更全面的查验。放在壁橱中加标点的《大经》虽然不如放置在圣所中的《大经》那样引人关注,但也有它们的长处。马加比的书也可能是有用的,也许应该很好地接受。我们符合教规书籍的残卷也非常珍贵,不太容易获得。因此我们应当对孟正气神父提到的、那些在大月和小月初或中旬诵读的书进行新的调查。我们不能从欧洲犹太人那里得到这方面的知识.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做法。因此我们期望从中国得到这些知识。我们希望,已经虚弱不堪的开封犹太会堂不至于像其他会堂一样与穆斯林教派合而为一,至少不要消失得无影无踪,使我们再也得不到它的消息。这样的担忧使得我们应该在中国更紧迫地工作。传教士也要求学者们向他们提供犹太人在受迫害期间上交中国官府的那本中文本书籍的译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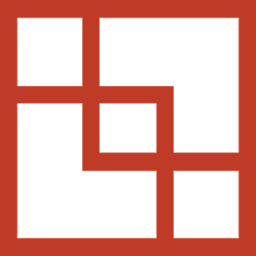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