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儒印题解
《天儒印》成书于1664年济南西堂,作者利安当。浙江嘉善魏学渠为之作序,淮阴尚祜卿作《天儒印说》。本书根据1664年刊梵蒂冈教廷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藏本编辑整理,共60面,文献编码为Borg.cine.334(9)号。[1]同馆藏还有一部,Borg.cine.349号;法国国家图书馆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亦有藏本,古郎(Maurice Courant)编目为7148号。
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字克敦,于1602年4月生在于西班牙,1618年3月入方济各会,1633年到达中国。不久因为中国礼仪之争,利安当离开中国,赴菲律宾征求神学家们的意见。后历经周折,于1649年重返中国,传教于山东济南。在近二十年里,他先后为五千中国人施洗,其中包括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在1664年天主教案中,利安当被捕入狱,备受诬妄。此书即是在利安当入狱后出版的,有为自己辩护之意。1666年, 他被遣往广州,囚禁于广州耶稣会旧会院内。三年后(1669)利安当在广东去世。
《天儒印》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是从天主教教义出发来阐释四书章句的。[2]例如,在解释《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把儒家日新不已的道理与天主教的洗礼和告解礼联系起来,用洗礼解释“荀日新”,用告解礼解释“日日新”,又用省察告解解释“又日新”。在解释《中庸》的“天命之谓性”时,释“天”为天主,并借此阐发草木、禽兽、人类的灵性之别,介绍天主教性教、书教、宠教的发展过程,说明天主教的超越性。在解释《论语》中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一语时,把“终”解释为“天学四终”,即死亡、审判、天堂、地狱。把“远”解释为善恶之报。从赏善罚恶的角度劝善警恶,谓之使民德归厚。在解释《孟子》中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一句时,他以信仰天主教的天民为先知先觉,号召他们以“舍我其谁”的精神,担负其觉后知、后觉,传扬天主教的重任。其中牵强附会之处也有不少,如把“亲民”解释为“爱人如己”之旨;把“至诚”解释为天主;把“有教无类”拆解为“有”教,即天主教是无始无终,超越诸教的唯一“有”教。可以说,这本书基本是借题发挥之作,即借四书的章句,阐发天主教的教义和礼仪,以达到传扬天主教信仰的目的。正如尚祜卿之子弼所言,“是书乃取四书之字句,有可以天主教道理诠解阐明者乃彙集而解。”也就是用“六经注我”的方法,对四书进行断章取义的解释。
这是因为,方济各会的会士们不认为中国人过去曾获得关于真正上帝的知识。因此,并不主张从儒家经典中寻找上帝信仰的印记,以此来引导中国人恢复上帝信仰。他们反对耶稣会士的会通儒教与天主教的作法,并且针对中国人以天儒不二拒绝天主教信仰的情况,利安当以及其会士教友们坚持天主教信仰的超越性,主张借儒家传统的尊君孝亲思想,因势利导,使中国人以“因性之理”明“超性之理”,信仰天主,敬拜天主,以明生前死后之事,三位一体之奥,报答天主救赎大恩,切实省察修行,得以死后升天。用尚祜卿的话说,就是“天主造物也,殆如原印之印楮帛。”“大主授其印乎,宣圣其承印者乎。”孔子之教是不能当作“原印”,去“印”万物的。孔子心源是天主降衷其中,孔子之圣是天主生之、纵之。因此,如果想成圣得救,就当撇下一切来皈依天主。
天儒印目录
天儒印序
一、西学儒学互为表里
余发未燥时,窃见先庶尝从诸西先生游。谈理测数,殚精极微。盖其学与孔孟之指相表里,非高域外之论,以惊世骇俗云尔也。
二、世人不识西学儒学之旨
顾世不察,以貌相者去而万里。或阳浮慕之,第肤掠其制作之工巧,与窜述其测算之法度而已。言文而不及理,言器而不及神,毋乃先失其孔孟之指,於体用何所取裁乎?
三、《天儒印》发扬《四书》之义
顷见利先生《天儒印》说,义幽而至显,道博而极正,与四子之书相得益彰。则孔孟复生,断必以正学崇之。使诸西先生生中国,犹夫濂洛关闽诸大儒之能翼圣教也。使濂洛关闽诸大儒出西土,犹夫诸西先生之能阐天教也。盖四海内外,同此天,则同此心,亦同此教也。今利先生处济上近圣人之居,必更有发扬全义,以益畅乎四子之指者,则儒家之体用益著云。
时康熙甲辰夏闰
浙嘉善魏学渠敬题
天儒印说
一、大主创造天地人物
粤稽大主全能,破分混沌,创立初人,畀以明德之性,启灵顺则,而天教於兹彰焉。以故大主之造物也,殆如朱印之印楮帛,楮制之印非可执之为印,斯乃印之迹耳。天地人物一切万事之理,皆天主迹也。使欲当之原印而复以印诸物不亦谬乎?
二、大主生、纵孔圣
想我哲人未萎,泰山梁木谁实诞之?聪明睿智实谁予之?谓非天生、天纵可乎?既曰天生、天纵,必有生之、纵之之主在焉。则尼山之心源,固维皇之降衷也。大主其授印者乎,宣圣其承印者乎。苟不问生、纵之由来,而徒知表章孔子,尊为立极之至范。虽非阿私所好,然执楮帛之印当原印,以印诸物,吾知至人复起,亦必辞而辟之矣。《记》云:“天子有善,让德于天。”矧知天、事天之大圣,司传木铎、觉世扶民,而又五德在躬,讵有不逊美于至善之天主者哉?
三、天儒同异考证
不肖从事主教多年,缘作吏山左,□拙被放,萍踪淹济。幸得侍坐于泰西利、汪两先生神父之侧,昕夕讲究天学渊微,得聆肯綮示。敢漫云入室,亦或引掖升堂?不同门外观矣。嗣此,益订天儒同异,多所发明,不肖爰有《补儒文告》暨《正学镠石》二书,将以就正同人,剞劂有待。
一日。利师出所解四子书一帙,且诏之曰:远人不解儒,略摘其合于天学者,而臆解之如此。然与,否与?不肖读竟,蹶然兴曰:吾侪类言天儒一理,若师所言理庸不一。倘溺于章句,而不深究,其指之南而以为之北奚一焉。今而後,谓四子之书即原印之印迹也可。于是名其帙曰《天儒印》。
天主降生一千六百六十四年
淮阴尚祜卿沐手敬书于济南之西堂并识
第一节 《大学》新解
一、明明德
《大学》云:“在明明德。”注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盖言吾人之灵明,不能自有,而为天主所畀也。明者,言当用吾明悟之推测,洞见本明之真源,以克全其初则;可以因固然而得其所以然,因万有而得夫万有之所从有也。
二、亲民
《大学》云:“在亲民。”“亲”之一字,甚切于天学爱人如己之旨也。注释作“新”者,但指有旧染之污而去之。此义包于亲内,则亲足兼新,而新不足以兼亲也,仍旧文自合。
三、止于至善
《大学》云:“在止于至善。”超性学论,惟天主可云至善,则至善即天主也。其曰止于至善者,谓得见天主之至善,而息止安所也。
四、知止而后有定
夫止者,吾人之向终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盖既知吾人究竟,即当止向天主,则定而静而安而虑矣。
五、虑而后得
“虑而后得者。”谓于目前而能豫筹身后之图,则有备无患,自得所止也。凡失天主为永祸,得天主为永福,得即得至善永福之天主也。
六、本末终始
《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本”即《中庸》所云“立天下之大本”“本”字。其谓本者,又即所云诚者自成,而道自道之义。盖未有天地之先,自立常在者之体,所谓本也。
而使物有宗、类、殊、独、依者,所谓“末”也。
其云终始,亦即诚者物之终始之谓。盖造天地万物,为之发端,而为之归结者。(天学《圣经》载,天地大尽时,宇宙灭劫。是时,天主审判生死。)惟此无始无终之主,能终始万物,所谓“事有终始”也。夫事物之主宰,惟此一主。先先而无元,后后而妙有。精理奥蕴,至道存焉。人能识认真主,以致其知,则先后了悟,而本末终始,罔不洞彻,不其近道乎?倘迷谬不知,根源一失,事事物物履错纷如。故又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七、日新不已
《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天学定初入门者,有领圣洗之礼。以圣水洗额,用盘承之,外涤其形,内涤其神。盖令人洁己求进,去旧以归新也。独以铭沐浴之盘者,若於领圣洗之礼有默符焉。
至于日新又新之说,是又天学悔解之义。凡领洗以涤除原罪也。此后又有本罪,或思或言或行,义士一日七落,恒人能免无过。倘不知解悔,则愆尤业积,所谓自作孽,不可活矣。是以天学复有告解之礼。
盖学者既欲洗涤己罪,必当日日定志,日日省察,日日克治,谦抑自下,吁主祈宥,敏策神功,补赎前愆,必诣于纯德后已,断不敢一日苟安,姑待之明日也。信能日新又新如是,吾主圣训所谓“活水溢于其腹”是也,可望沾圣宠获常生矣。洗解二规,圣教旷恩,缺一不可。有志洗心者,或亦读盘铭而兴起也乎。
第二节 《中庸》新解
一、天命之谓性
《中庸》云:“天命之谓性。”
此“天”字与本章“天地位焉”之“天”不同。彼指苍苍者言,此指无形之天,即天主是也。
所谓性者,言天主生成万物,各赋以所当有之性。如草木则赋之以生性,禽兽则赋之以觉且生之性,人类则赋之以灵而且觉、生之性焉。
天主初命人性时,即以十诫道理铭刻人之性中。而人各有生之初,莫不各有当然之则,所谓性教也。以故趋善避恶,不虑而知,岂非秉□□然哉!人能率循性教,可无违道之讥。
奈性久沦晦,人难率循。于是又有书教,以十诫规条,刊列于石,令中古圣人以宣示之,俾人率性而行,遵如大路,所谓道也。
迨世风日下,人欲横流,书教又不足以胜之。及至天主降生赎世,亲立身教,阐扬大道,普拯群生,使天下人皆得性教原本,而教术始咸正无缺矣。夫合性书二教,而为身教,此属吾主宠教,恩施于此尤挚。迄今圣教彰明,天命实式临之,敢曰不钦若承之哉?
二、及其至也
《中庸》云:“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盖言惟天主则无所不知也。
又云:“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盖言惟天主则无所不能也。
又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天渊、鱼鸟,何一非造物主之化生、所充贯乎?上下察者,非以明天主无所不在之义乎?
三、造端乎夫妇
《中庸》云:“造端乎夫妇。”天主创生人类,其始惟一男一女。结为夫妇配偶,令其传生,是为万世人类之元祖。所为造端也,此人生之所来也。
又云:“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吾人之终尽时,必有所至之处。不在天上,则在地下,无世界中立之理。《论语》亦云:“君子上达,小人下达。”盖示人以察之之意,此又人身后之所由往也。
四、鬼神之盛德
《中庸》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
浑言之,凡无形无声而具灵体者,总称曰鬼神。分言之,则正者谓神,即圣教所云天神是;邪者谓鬼,即圣教所云魔鬼。
是德之盛,当就天神言。盖天神有九品,有侍立天主者,有运动诸天者,有获守国土、郡邑、人物者。然皆承行天主之旨,无敢违也。若鬼邪悖叛真主,受苦罚之永殃,虽间容在世者,惟以诱陷人类为务,何德盛之有?
其云“体物不可遗”者,凡人皆主造生,凡人皆主保存,故凡一人咸有一天神护守之,如纳赤子于襁褓中也。
天神无形无声,故曰:“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然曰视之听之,实有一天神领守我者,以日施其照护引治,而迪人于正道也。然则人宜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惟神是式是训,无负上主仁慈之所托可也。奈何因其弗见弗闻,而遗于所体之外乎?释此,并知体物不遗,自是正神德爱。鬼邪既务诱陷,尚可言体物耶?故鬼自鬼,神自神,别其邪正,则判然矣,乌容并列而混称之也。
五、惟至诚能尽性
《中庸》云:“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所谓至诚即天主也。盖金石无生,草木无觉,禽兽无灵,人类无全神体,天神无最纯之神体。故就其本性,虽各圆满,然终属有限,不可谓之尽。惟天主则全能、全知、全善,本性充然尽足且也。生人则赋以灵兼生觉之性,而人性无不全焉。生物,则赋草木以生性,赋禽兽以觉且生之性,而物性无不全焉。生天地,则赋天地以化育之功用。
六、参赞天地化育
而其所以化育者,实由天主默相乎其间,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也。然化育所以然之妙,精深莫测,人第就诸天之运动,大地之发生,一想像之,孰主张是孰安排是,必有立乎天地之先而宰制之者。从此由见窥隐,由显察微,则有以得其故矣,故曰:“则可与天地参矣。”
七、至诚可以前知
《中庸》云:“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天下一切未来之事,虽神人不能预测,惟无所不知之天主能知之耳。即天学中诸圣人,亦多有前知者,然非本力所能,咸由天主默启而得之。况至诚曰道,乃可前知。今人奈何以推算占卜之伪术,而求驾于上主之智能乎?亦诞妄极矣。
八、自成与自道
《中庸》云:“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万物不能自成,俱受成于天主。惟天主则灵明自立,而不受成于万物,故曰自成。天主凡所行为,皆由本性之欲,而行其所欲行,绝无有引于先,而能道之者;亦无有从于後,而能践之者,故曰自道。
九、诚者为物之始终
凡物有有始有终者,有有始无终者,惟天主无始无终。无始,是以能始物,而为物之始;无终,是以能终物,而为物之终。故曰:“诚者,物之终始。”
十、不诚无物
若非天主授物以有,则物岂能自有哉?故曰:“不诚无物。”
十一、诚者成物
诚之为贵者,言君子惟尊贵此诚,即天学钦崇一天主于万有之上之意也。天主为万物从生之大原,既生之後,复无物不保存照护之,故曰:“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十二、成己成物之德
天主万德悉备,咸具微妙灵明之性。故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
十三、合内外之首
天主既生万有于外,视未生万有所内含之元则无以异,故曰:“合外内之道也。”
十四、时措之宜
迨乎造物之时,既至则无形与有形咸造,而物物各予以当然之宜,故曰:“时措之宜也。”
十五、天地之道
《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夫天地特一物也,曰天曰地,已二之矣,曷云不贰?盖言惟一主宰化生天地万物云尔,非人所可思议也。故不言天地为物不贰,生物不测;而言天地之道其为物不贰,其生物不测。两其字,明指出天主矣。悟及此,则天地之道岂不可言尽乎?
十六、维天之命
《中庸》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今人误认形天,辄施崇奉,不知形天特覆物之一大器具也,固有所以为天者存。所以为天者非即天主乎?否则“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岂形天之所有哉?
十七、圣人之道
《中庸》云:“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洋洋”云者,言天主之全能无不充满,而万物因之以发育也。
天主虽无所不在,而静天之上,尤为发现之所。且此天为万物之界,此外则无物矣。故曰:“峻极于天。”然何以曰“圣人之道”。盖圣人奉此,以为行路之准也。
十八、天地之所以为大者
《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并育矣,而不相害,孰使之不相害乎?并行矣,而不相悖,孰使之不相悖乎?必有所以然者以宰制之。故物物各有私所以然,是为小德之川流;而又有一总所以然,是为大德之敦化。此乃天地之所以为大。所以为大者,是即天主耳。
十九、至诚者能经纶天下之大经
《中庸》云:“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
所云“能”者,言惟天主有此力量也。
“大经”者,天地神万物之秩序也。
“经”者,言限定各物之全性,而使之同一宗类也。纶者,言各类分界之,而使之成特一,因以共成某类也。
二十、立天下之大本者
又云:“立天下之大本。”本者,所以然之谓也。凡物有三所以然,曰私所以然,曰公所以然,曰至公所以然。如父母为人之私所以然,主宰一家者也。如君王为人之公所以然,主宰一国者也。二者名曰小本。天主为万有之至公所以然,名曰大本,是人类之大父,乾坤之共君,主宰天地万物者也。盖天地万物,咸因此而生,如草木之有根也,岂非立天下之大本乎?
二十一、知天地之化育者
又云:“知天地之化育。”凡格物穷理者,皆知其妙,而究莫知其所以妙。惟生天地者,始洞彻其情。知者,有生养保存之义。如今知府知县之知,非徒知之,实主之也。
二十二、天主无所倚
凡受造之物,不论有形无形,皆有自立依赖二者,惟天主则至纯神自立,绝无依赖,故曰:“夫焉有所倚?”
二十三、肫肫、渊渊、浩浩
《中庸》云:“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
天主生天以覆人,生地以载人,生万物以养人。其于人之有罪应罚者,亦不遽加,而俟其痛悔迁改。虽不废至正至严之义,然正义之责终不逾其慈爱之锡,非肫肫其仁乎?此虽不言降生代赎,而己若为降生代赎,示其意也者。
天主妙有美好,深微无极,非神人识量所能尽识。故以受造之美好,与天主之原美好较,犹大海之一滴而已,非渊渊其渊乎?
九重天之上,别有永静天为万福之所,此天为天主发现,及诸天神诸圣人受真福之处,广大无比。以永静天视九重天以下之世界,正犹以世界视母腹中也,非浩浩其天乎?
二十四、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中庸》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静天之上是谓上天,所云天堂是也。地言载者,谓足所履处。上天亦言载,则知吾人本家不在世在天,是上天实人生身後之持载。戴于斯,履于斯矣。故曰:“上天之载。”
其云“无声无臭”者,人之身後,形徂气散,灵神独存,而可至于上天者,惟此灵神耳。四元行土上为水,水上为气,气上为火,至火域已无气矣。火上为七政列星之天,又上之静天,非复形气可蹑,故云:“无声无臭”是也。
其云“至”者,神至而非气至也。释此,推知吾人在世如行旅然,皆行其所当至之域,非即其已至之域也。惟至于天上国,所谓万福之所,则为至于本家矣。
第三节 《论语》新解
一、巧言令色
《论语》云:“巧言令色,鲜矣仁。”凡异端邪教,惑人听闻,令人持斋念佛,外面装饰善貌,诓人皈依,都是巧言令色之类,诱人获罪,陷人永苦,於以杀害天下万世之灵神而罔恤也。所谓外着羊皮,而心怀豺狼者也,岂非不仁之极乎。
二、慎终追远
《论语》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终”者,即天学所云四终也。一身死,二审判,三天堂,四地狱也。
“远”者,言一生之所思、所言、所行,虽久远而必有善恶之报也。
人若常念其终,而慎谨之;常追思其往昔所有之是非,而省克之。则凛于圣诫,有所为善而不敢为恶,民德其归厚乎。
三、攻乎异端
《论语》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异端之说,其初害及其身,人不审察,眩瞀而从之,则尽人而为其所陷矣。夫世有三仇,魔居其一。凡浸淫于异端,而为其所煽惑者,悉魔仇之害也。其惨祸人心,可胜言哉?及深中其害,而为之辞曰:罪在异端。
大主赐人明悟,令人推论是非,择别邪正者为何也?岂非自贻伊惑耶?孔子所为不咎异端,而咎攻之者,非宽异端也。异端不足惜,可惜者攻之者也。吾儒动言训法孔子,然师训尔勿攻,而尔听之欤?胡今之为释迦、道陵仆仆者多是,诵法孔子之人也不亦大可怜欤?
四、朝闻夕死
《论语》云“朝闻道,夕死可矣。”
所谓“道”者,即生死之正道,非轮回之妄说也。盖不闻道之人,无论生不可,即死亦未可。生则贸贸,死入永苦。若闻道之人,生虽受艰苦,死後必受永福矣。
其云“朝夕”者,人寿纵百年,不过一朝夕事耳。露电浮生,转瞬危迫,如何亟亟闻道以无负兹朝夕,可不猛思痛醒也哉?
五、无所祷之罪
《论语》云:“获罪於天,无所祷也。”
此“天”非指形天,亦非注云:“天者理而已。”盖形天既为形器,而理又为天主所赋之规则。所云获罪于天者,谓得罪于天主也,岂祷于奥灶所能免其罪哉?
然孔子斯言非绝人以祷之之辞,正欲人知专有所祷也。观他日弟子请祷,但曰:“丘之祷久矣。”宁云己德行无丑,而不必祷,正谓朝夕祈求天主而赦我往愆也。合而论之,一不祷于奥灶,而言天以正之;一不祷于神祗,而言祷久以拒之。
然则孔子之所祷,盖在天矣。故其言曰:“吾谁欺,欺天乎?”又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则孔子未尝不以天祷为兢兢也。乃孔氏之徒祈神佞佛,所谓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窃恐获罪于天矣。
六、笃信好学
《论语》云:“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向主有三德,曰圣信,曰圣望,曰圣爱。而望爱必以信为基,故《十二信经》咸以我信为启迪之要,良繇圣教真理,大主觌面授之,历代圣人,公见公闻传之。其理诚笃无伪,其言笃实不欺。吾党学者,第宜一心笃信,而无容疑贰,无容摇惑者也。
明悟既彻,则爱欲所锺,惟当精思好学以求其理。诸凡规诫所昭,训典所垂,尊持而佩服之,用为省察克治之功。念兹在兹,罔有益斁兹,所为笃信而好学也。
夫信好若是其专者何也?盖万物真宗惟一、大主,是为人类之所切向。每念其救世降赎之恩,慈爱群生,穷天罄地,靡可为报。惟有以爱还爱,以死还死而已。是故为义而被窘难,或有异端魔仇之倾害,或有暴君污吏之摧残,则宁失天下福,宁罹天下万苦,而不敢少得罪于吾至尊至善之主。有如白刃可蹈,匹夫不可夺志是也。夫死忠死孝,世容有不得其正,未合于道者。而惟为天主致命,则死于钦崇,以一死而炳耀天国,於道为至善矣。所谓守死而善道也。
七、天纵之圣
《论语》云:“固天纵之将圣。”
释此,知孔子之得成其圣者,非孔子自能,而由天主阴隙之也。故孔子尝言“天生德于予”,则亦知阴隙之所自来矣。
维仪封人亦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并知孔子之司教铎而传宣者,秉于上天之命也。今学者既知尊孔子矣,而不知钦崇纵孔子之圣者谁属,命孔子之为木铎者谁属,谓孔子之徒乎?
八、事人与事鬼
《论语》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盖非鬼而祭,孔子既以为谄,则邪魔必为其所厌绝。而事神之理,人又未易晓彻,则且就臣事君、子事父者言之。此人事之当然,不容不事者也。而况合天下万国之大父大君,当何如事之哉?故不言所以事神,而言事人,正精于言事神也。
又云:“未知生,焉知死。”言人既不知人之生为天主赋人之灵魂与形骸缔结而生,又焉知人之死为天主收人之灵魂与形骸相离而死乎?苟能知生之所由来,则有以究初人肇造之恩,即能知死之所终向,而可以悟灵神不灭之理。故不言所以知死,而言知生,正精于言知死也,惟在人深思而自得之。
九、不疚则不忧不惧
《论语》云:“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人生涉世,恒履多忧多惧之地;而诱感所加,类生可忧可惧之情。求其不忧惧难矣。盖疚恶丛心,二罪纠缠,三仇攻害,事事拂理,种种违天。故其在安乐,乃其所以为危苦也;在饱饫,乃其所以为饥渴也;在欢笑,乃其所以为涕泣也。
今世之忧惧暂且短,来世之忧惧实深且长。何者?疚恶者,忧惧之根也。疚恶不种,忧惧不殖矣。虽然,忧惧亦曷可少乎?人惟狃佚欲、耽晏乐,则莫知忧惧,何繇省察已过,而克免于疚?
惟夫知忧知惧,则潜痹隐慝不容留伏于心意之间,仰不愧,俯不怍。始于忧惧,而卒于无忧惧。由是生顺殁宁,诣于常生,而永苦不足以撄之,夫可忧惧之有哉?孔子又云:“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故内省尤必期于内讼。盖内讼则以其所追省者露其丑于严主之台前,或可望其慈恕,不我再鞠也。不然,吾未知其忧惧果能释然否也。
十、远虑近忧
《论语》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注云:“虑不在千里之外,则虑必在几席之下。”余亦云:“虑不在世事之外,则身後永苦之忧必在枕席之下矣。”
十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论语》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吾主圣训,曾有是语,此即“爱人如己”之大旨也。
盖不欲有二:有肉身所不欲者,有灵神所不欲者。肉身之所不欲如饥、寒、病、苦诸拂逆等事,灵神之所不欲如贪、淫、忿、诈诸恶慝等情,载在《十诫》、《七克》、《十四哀矜》。诸书可考也。
盖两情相絜,一理互揆,彼此均爱无揆尔我,所谓恕也。故恕训如心,如其爱己之心,则爱人如己矣。
然言不欲勿施,未言所欲则施。倘己所欲者邪情邪事,而以施之于人,是又害人如己也。
故善言爱者,必体天主之爱人以行其爱,而後可以言“爱人如己”,则爱人即所以爱天主也。果如是,则一言而可以终身行。行此一言,而可以惬圣旨,承真福矣。
奈何世情迷谬,其求诸己者,惟曲济其所欲;而其施于人者,恒皆己所不欲之事。不思我施人,人亦反而施之。则不惟不知爱人,并亦不知爱己矣。
所以《中庸》言“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不愿,亦勿施于人,岂非有得于“爱人如己”之理,而为之一发明也哉。他日曾子称孔子之道,亦曰“忠恕而已矣。”
夫忠者,臣爱君之称;恕者,即不欲勿施,人己相爱之义。天主既为天地大君,不爱天主可谓忠乎?欲爱天主,而不爱天主所爱之人,可谓恕乎?故所云忠者,即圣诫所谓“爱天主万有之上”;所云恕者,即圣诫所谓“爱人如己”是也。爱主爱人,如南北两极不容缺一。不爱主,断不能爱人;不爱人,称不得爱主。先儒曾言:“无忠做恕不出。”此语可谓得其旨矣。但学者莫不知有夫子之道,试于忠恕二义而究心焉,其或庶几于天学乎?
十二、不尤不怨
《论语》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盖世福不齐,上主不必均畀。其或此丰彼啬,似天有偏私,则怨天矣。
世欲无厌。上主不容曲徇,其或此愉彼拂,似人有奇遭,则尤人矣。曷思富贵云影,功名石火,穷通得丧,造化自有秘密,怨尤徒生觖望。谚有云:“怨天者不勤,尤人者无志。”
君子为己之学,曾如是乎?是以刻苦精修之士,惟知以昭事真主为宗,以广爱行仁为本,以克己寡过为切务,以生死令终为究竟。其于世境浮荣毫不萦心,则其退藏笃造之诣人所不见,而上主于重玄之际鉴观冥漠,庸有不彻尔志、歆尔勤者乎?
所谓下学上达知我其天,信不诬也。夫大主全知,无有人隐不在其洞照中者。然而下学上达者蔑闻,怨天尤人者概见,徒曰天不知我。天焉不知尔怨矣,知尔尤矣,知尔弗之学,弗之达矣?第恐如此而为天主所知,异日尔将自怨自尤之不暇。虽欲冀天主之莫我知也,何可得乎?
十三、仁与水火
《论语》云:“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夫杀身成仁,所在俱有,曷言未见蹈仁而死者?盖言若为爱天主与为爱人如己之仁而死,则形躯虽死,而灵魂得常生之福于天上国也。
夫水火,本天主所生以养人之具,而不善用之,即为害人之具。彼世间之功名富贵等,犹水火也。善用之,即为事主爱人之具;不善用之,未始不为水之溺人、火焚人者矣。
十四、有教无类
《论语》云:“有教无类。”天下一切教术,皆人为,皆後立,虽名为教,不名有教。惟天主自无始有,教亦自无始有。故有性教,有书教,有身教。主有教,有始于无始,终于无终,独名有教,非他教可比絜也。
且诸教或儒或释或道,各于其类,强之使同,弗或同也。故曰:“道不同不相为谋。”惟主惟一,教亦惟一。故上自王公,下逮士庶,无论贪富,无论贵贱,无论长幼男女,无一人不在天主圣养中,则无一人不在天主教诫中。统此人类,统此圣教,故谓有教无类。此圣教会为额格勒西亚有圣而公也。
第四节 《孟子》新解
一、善恶之机
《孟子》云:“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
盖人生初始,一无字素简耳。举西子,况素质也。蒙不洁,如素简之受点染,况素质为罪垢所污也。凡人一经罪垢业集,外虽饰其容上,其内灵之丑秽,特甚掩鼻而过,不亦宜乎?夫天主生人生善,不生恶。今兹恶人,即前此西子,特蒙不洁则为恶人矣。
勿曰恶人,天之弃人,竟灭心主宥,而不一哀恳吁祷也。倘翻然悔改,依赖圣恩,遵大小之斋期,守二五之诫训,承法浴之水,沐浴以洗涤其心志,则天主必矜怜而释之矣。
昔吾主设喻,谓人有百羊,偶亡其一,则必遍觅之。既得,则负以返,聚邻友共为之庆也。盖九十九羊,善人也;所亡羊,罪人也。得善人九十九不足喜,得一罪人回心向道则喜宜倍矣。故曰:“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上帝者,即主宰万有,至尊无二之天主也。然则人不向望天主,将谁望哉?
二、以道觉民
《孟子》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後知,使先觉觉後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盖伊尹之言如此。
然曰“天生此民”,则知人类造生,厥有始矣。
曰“先知後知”、“先觉後觉”,则知降衷于民,厥有自矣。知觉虽有先後,及其既知既觉,无二知觉。则知天所赋予,厥维均矣。然而重其责于先觉者。盖斯道遮隔于迷谬,而披示于明悟者。同是天民,莫不同秉天道,故以斯道觉斯民,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
其云“非予觉之而谁”。盖使先知觉後知,使先觉觉後觉,天实使之,庸敢诿诸?然则觉世岂人力也哉?今斯民大寐久矣,呼而使之寤,此其时矣。愿我天民又为後知者之先知,後觉者之先觉,其克有当干天意乎?
三、天将大任于是人
《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由是观之,舜说诸人,所肩不过世任,犹必始困终亨,况吾人欲希心最上事业?此其为任,尤其至大极重者,而欲以富贵安亨致之,必不得之数也。盖天国之分,非恃人力可能,故以巨绳穿针孔尚易,而以富贵进天国实难也。
是以人欲求天降大任,其心志体肤身行等,必若是苦劳饥饿空乏拂乱诸态,种种备尝。惟其所动忍,而坚心设性以承之。由是,苦劳我者,将安逸我也;饿乏我者,将饱饫我也;拂乱我者,将顺适我也。于以增我神力,益我圣宠,而任人可以克荷大任,何患其不能哉!
故孟子又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夫人莫不慕安乐而恶忧患,讵知忧患者,荣福之基乎?安乐者,殃苦之胎乎?生于忧患,是即常生;死于安乐,是即永死。忧乐二门,决招生死二路,人奈何不以苦劳重直,售天上之大业乎?
四、尽心知性以知天
《孟子》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盖言人能尽心以格物穷理,则知吾有形之身,有无形之灵性。既知吾有此灵性,即可知畀吾灵性之天主矣。
又云:“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盖言吾性不自有,有授吾之性者;吾心不自有,有予我之心者。存心,非欲侈自心之广大;养性,非欲侈自性之神奇;正欲不失其赋畀心性之本原耳。故曰:“所以事天也。”又云:“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夫人生在世,无论寿修夭折,皆不免死;所异者,修为不同耳。惟当修身克已,以静听主命,此天学以善备死候为向终之上范也。至于数之修短,岂贤所顾问哉?
[1] 辑入《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篇第二册,载《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66-67影印版。
[2] 方豪揭示,《天儒印》其拉丁文译名曰:(Concordantia legis divinae cun quatuor libris Sinicis),如果再译回汉文,应作《天主教与中国四书之对照》。
本文由汉语基督教研究网[ChineseCS.cc]—汉语基督教文献馆[CCT.ChineseCS.cc]发布。该文章由本站收集、整理、录入!请勿他用,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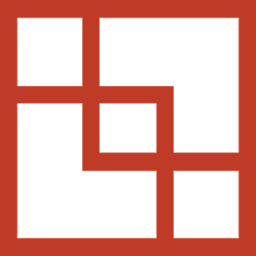
评论